花都獅嶺皮革皮具打工者心態調研
作者:百檢網 時間:2022-02-11 來源:互聯網
近年來,廣州用工形式越來越撲朔迷離。從2011年第四季度以來,“用工難”基本已經成為普遍的共識,來自人社部門和企業的反饋都顯示出,用工需求并未減少,外來工總量卻在毋庸置疑的下降,今年開年以來,這種形勢愈發明顯。即便政府部門仍然不肯改口直承“用工荒”,但是,除了一直存在的所謂結構性矛盾,現在供求矛盾已經凸顯,甚至對廣州的城市發展、社會生活以及產業升級轉型等方方面面造成影響。
我們一直在關注這一現象。因此,我們發起“透視廣州用工困局”的系列報道,不再流于對用工現象的描述,甚至不再糾纏于數據,在這個系列的策劃中,我們將選取多個樣本,從不同角度解剖,以期得出*全面的結論:廣州到底用工難不難?為什么難?難在哪里?對廣州的深遠影響在何處?
本期,我們的樣本來自花都區獅嶺鎮的皮革皮具工人們。作為皮革皮具產業聚集地,花都獅嶺鎮是一個很重要的典型。打工者的群像也許很難以偏概全,不過,這個樣本的意義在于:當下的打工者,他們會是怎樣的心態?“離開這間廠房,或者留在廣州,也許只要一個很簡單的理由。”他們說,十幾個一起打拼的同鄉今年只回來幾個,不管是哪種選擇,當生存不是那么艱難的時候,去留也顯得更加隨性。
樣本1
過度加班擔心“有命賺錢沒命花”
姓名:阿彪
籍貫:廣東茂名
曾工作過的地區:花都、東莞、白云
位于花都獅嶺的人力資源中心,一排排藍色的大帳篷下,都是正在招聘的企業。元宵節已經過了近10天,但是每天進場招工的企業還有300多家,他們都在急切地向過往應聘者“推銷”。而應聘者們則大多還在慢慢挑選中。
沿著一長排的攤位走過,來自茂名農村的阿彪和同鄉也在比對著各廠給出的條件。出生于156 0190 2607年的阿彪2004年初中畢業后就來到廣州,在花都新華的一家皮具廠工作。一年半后,他去了東莞。“東莞的工資沒有廣州高。”僅在東莞待了3個月,阿彪又回到了廣州。這次他的工作地點是皮具之都——花都獅嶺。后來幾年,他又換了幾個工廠,**相同的是都做皮具這一行。
2011年,阿彪到了白云區一家皮具廠工作。“加班時間太長,半個月只能放**假,太辛苦。”阿彪在那家工廠當板房臺面,每個月的工資是2500元,包吃包住,但每天從早上8點上班直到晚上11點才能下班。“雖然有加班費,但是我寧可多些時間休息、自由活動,擔心有命賺錢沒命花。”阿彪是家里**的孩子,父親是建筑工人,母親在家里種地,父母的收入足夠維持生活,他現在并不希望自己為了掙這點錢而把身體拖垮。
因此,阿彪決定離開白云區的工廠,再次回到獅嶺。“我希望找到一份正規一點的工作,每個月至少休息4天,**工作時間不要超過11小時,工資在2500元—3000元之間。”
樣本2
“找不到合適的,就去外地試試”
姓名:唐忠
籍貫:湖南
曾工作過的地區:花都
同樣是元宵節后才到廣州的唐忠,是一名湖南籍的農民工,出生于1982年,他也在人才市場中尋找著他的目標。唐忠告訴記者,他去年工作的一家小皮具廠,現在由于回流的工人太少而無法開工,“我去年在這里工作的十幾位同鄉,今年回來的只有六個人,其他都留在當地,或做生意,或去電子廠打工了”。
“和我干同一工種的,勤快的一個月都能拿到四五千元了”,唐忠也希望自己在新的工廠能夠拿到這樣的工資,同時還能夠有好一點的生活環境,多一些放假時間,“萬一找不到,我可能就去深圳或者東莞了。”
◎解析◎
價值參照體系已改變80、90后不太滿意打工生活
關于打工心態變化
“除了戶籍身份,他們(外來工)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某企業人力資源部門負責人這樣說,招聘者必須認清楚這一點,才能更有效率地為企業招人,“如果還是把對他們的認識停留在對他們父輩的印象中,可能就會出現偏差。”
目前,80后、90后已經成為外來務工者的主體。他們的父輩以農業收入為參照,對打工的耐受度相當高,“在老家種地,一年就1000多元的收入,當時出來打工,一個月能掙好幾百,省吃儉用下來,一年寄回去的錢,很讓村里人羨慕。”來自四川的黃永清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來到廣州打工,當初隨著一批老鄉一起前來打拼的他,如今已經回到老家農村。新一代外來工群體所對比的是身邊的打工者,甚至是城市打工者的收入,他們對打工生活的滿意度不高。
關于收入
“工資比老家只高幾百元這點錢不夠開銷”
工資沒啥吸引力,是很多外來工棄廣州而去的重要原因。在今年開春的“2012春風行動”首場招聘會上,對企業開出工資不滿的求職者比比皆是。
“月工資3000元以下的企業我都不考慮。”當了13年**焊工的王先生在招聘現場逛了一圈后無奈地發現合適自己工作的工資實在難以接受。王先生是四川瀘州人,他希望能找到月薪4000元以上的工作。之前招聘會有企業提供了保底3200元的工作,他并沒有答應,豈料這次招聘會上企業工資更低。“之前在老家的工資都差不多4000元,在四川這種工作很好找的。”王先生說。
無獨有偶,來自湖北江陵的方先生也表示廣州工資沒有競爭力。“我爸前幾天打電話過來,要我回家,說在江陵做汽車裝備也可以拿到2000多元的工資。”他告訴記者,自己2006年在廣州做汽車裝備工作,也只能拿2400元左右的工資,不如回家。“畢竟在城市中心,交通便利,而且娛樂什么的也方便出門,所以我們不想住工廠的宿舍,幾個人分攤房租也能接受,周圍吃的東西也多,現在城中村改造了,便宜的房子租也租不到,要是工資不理想,錢還不夠租房的,只能回去工廠的宿舍住。”他表示,自己來廣州是為了見世面,學習新知識,“遲早都會回家。”
“除了掙錢還需要自己的空間”
關于加班
就像樣本中阿彪所說的,新一代打工者,對于加班的態度是,擔心“有命賺錢沒命花”。加班是勞動密集型企業一直存在的現象,為何近幾年過度加班的問題不斷被提及?
專家認為,一方面,老一輩打工者耐受度較高,為了給家里攢錢蓋房子、給兒子辦親事,什么苦都能吃,加班就意味著有更多的工錢,所以他們的積*性也高。新一代打工者,則有強烈的個人空間意識,需要自己的生活娛樂交際,他們不愿意過度加班,“自己掙錢自己花,不承擔養家糊口的責任”;另一方面,新一代的打工者,維護個人權益的意識正在覺醒,被要求過度加班的時候,他們會選擇合理的方式維權。
在昨天的采訪中,獅嶺鎮某皮革皮具企業負責人也這樣說,80后、90后,與60后、70后幾乎是兩種不同類型。60后、70后的外來務工者是為了養家糊口才背井離鄉出來打工。該負責人也是一名70后,他以自己為例說,“我們以前出來工作,都希望自己能夠干出成績,干得出色,以期得到老板的肯定。”他認為,80后、90后定位不清晰,較之上一代,他們對工作的追求是,“沒壓力、舒適、好玩,不喜歡被條條框框和各種制度約束、限制,比如能夠多一些時間上網,和朋友出去放松”。雖然企業的工作環境在不斷改善,但仍然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
“不開心就走人換個環境很正常”
關于壓力
花都某公司總經理熊金紅表示,作為皮具皮革行業的聚集地,獅嶺的企業數量多,用工需求大,節后回流了大概80%。熊金紅認為,現在80后、90后的員工更加追求個性的生活,沒有溫飽之憂,往往不會為了一個月2000多元的工資在一個地方呆幾年;而由于計劃生育,他們這一代人家里往往孩子也不多,在家里就是寶貝,從小就被寵愛,難以承受太多的壓力。
在吸引打工者方面,今年不少招聘企業也落足心思。在某招聘會現場可以看到,企業紛紛把工作環境作為吸引人才的手段,在宣傳海報上標明企業有網球、羽毛球等各類體育設施,電視室、圖書館、瑜伽室、舞廳等文化娛樂設施一應俱全。能不能上網、宿舍有沒有空調都標得一清二楚。某美容美發設備有限公司的負責人張先生坦言:“過去誰出工資高就到誰那,現在即便別人出的錢不夠我高,但是能提供宿舍上網條件,員工可能會選擇跳槽。”
“有時候也不是因為這間廠不好,甚至新去的工廠工資也沒有更高,就是單純換個環境,或者熟悉的一起打工的同伴走了,自己也想跟著去而已。”白云區某電子加工企業打工者小張說,“有時候跟車間主管相處得不是很開心,就換個廠,反正附近的廠工作都差不多,我們做了幾年都是屬于熟練工,總是有人要的。”他說,也許會去深圳看看,總在一個地方也沒什么意思。
百檢網專注于為第三方檢測機構以及中小微企業搭建互聯網+檢測電商服務平臺,是一個創新模式的檢驗檢測服務網站。百檢網致力于為企業提供便捷、高效的檢測服務,簡化檢測流程,提升檢測服務效率,利用互聯網+檢測電商,為客戶提供多樣化選擇,從根本上降低檢測成本提升時間效率,打破行業壁壘,打造出行業創新的檢測平臺。
百檢能給您帶來哪些改變?
1、檢測行業全覆蓋,滿足不同的檢測;
2、實驗室全覆蓋,就近分配本地化檢測;
3、工程師一對一服務,讓檢測更精準;
4、免費初檢,初檢不收取檢測費用;
5、自助下單 快遞免費上門取樣;
6、周期短,費用低,服務周到;
7、擁有CMA、CNAS、CAL等權威資質;
8、檢測報告權威有效、中國通用;
客戶案例展示
相關商品
相關資訊

暫無相關資訊
行業熱點
版權與免責聲明
①本網注名來源于“互聯網”的所有作品,版權歸原作者或者來源機構所有,如果有涉及作品內容、版權等問題,請在作品發表之日起一個月內與本網聯系,聯系郵箱service@baijiantest.com,否則視為默認百檢網有權進行轉載。
②本網注名來源于“百檢網”的所有作品,版權歸百檢網所有,未經本網授權不得轉載、摘編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想要轉載本網作品,請聯系:service@baijiantest.com。已獲本網授權的作品,應在授權范圍內使用,并注明"來源:百檢網"。違者本網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③本網所載作品僅代表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百檢立場,用戶需作出獨立判斷,如有異議或投訴,請聯系service@baijiantest.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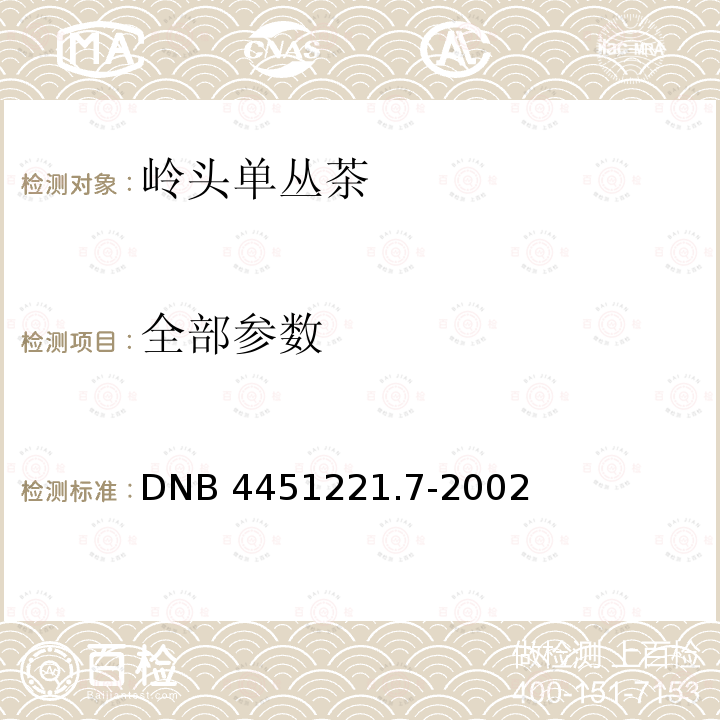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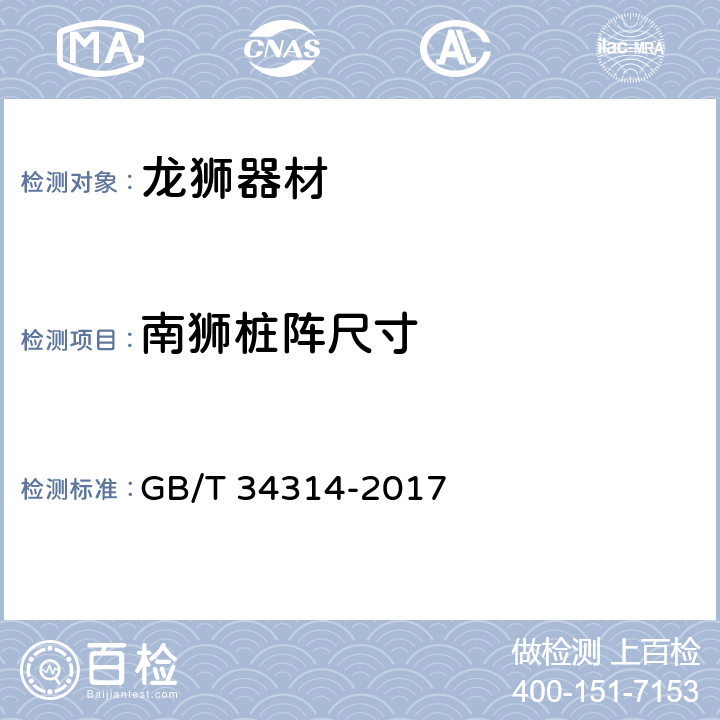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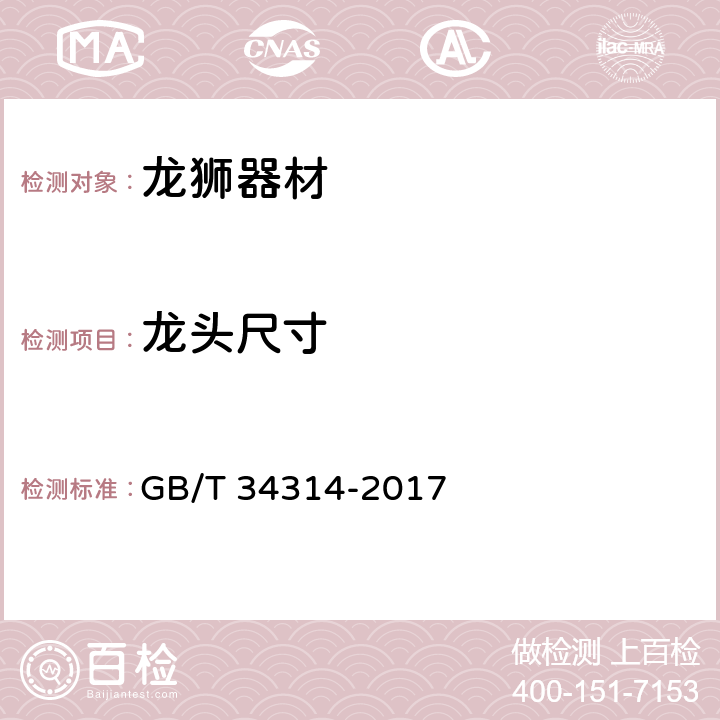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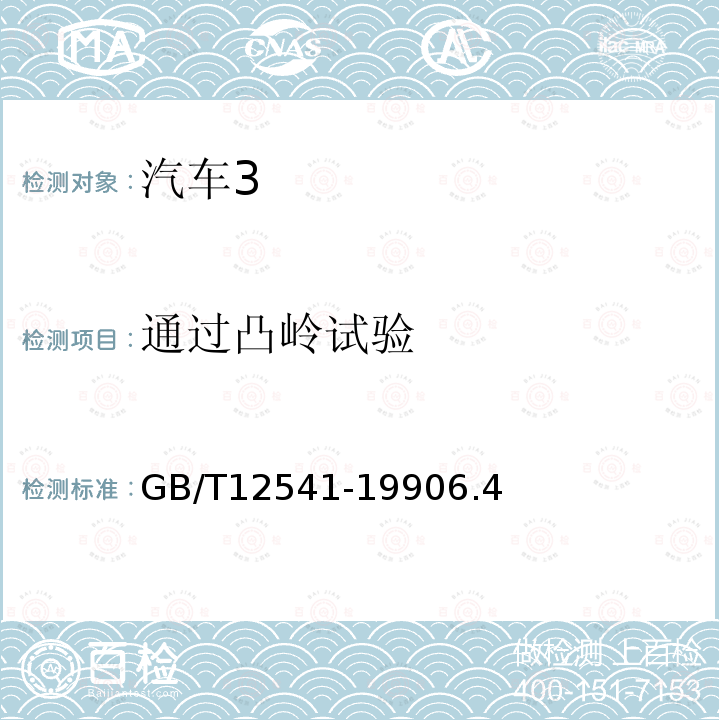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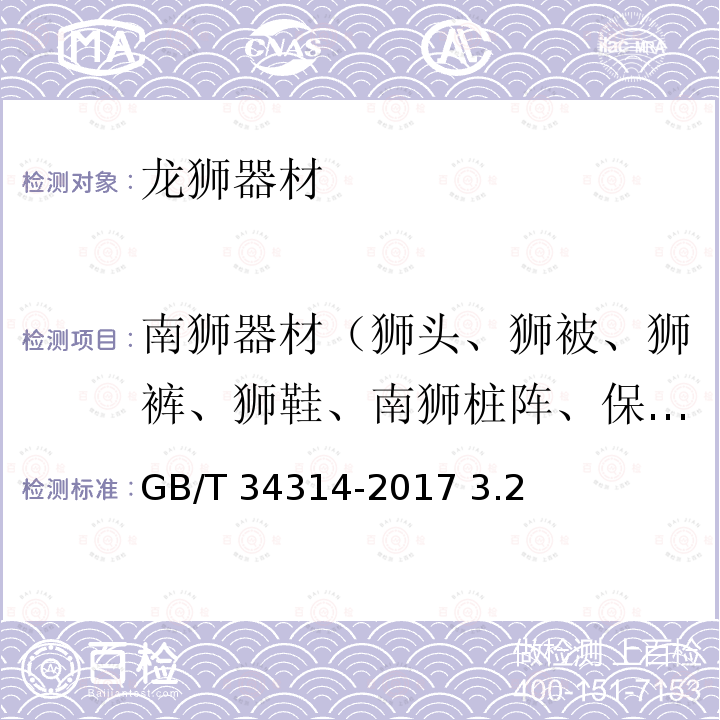








 400-101-7153
400-101-7153 15201733840
152017338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