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漁民:現在一年打的魚,還沒以前一個月多
作者:百檢網 時間:2021-11-15 來源:互聯網
>>> 捕撈量
長江的天然捕撈量在逐年遞減,由1954年的54萬噸,變為了近年來的10萬噸,不到全國漁業產量的1%。
>>> 物種數
長江已知物種1778種,其中魚類378種,長江特有魚類為142種,20多種魚類被列入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長江的國家一級保護水生野生動物數量在我國淡水一級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名錄中占2/3。目前一些珍稀、瀕危水生野生動物如白鰭豚、白鱘、長江鰣魚等已瀕臨絕跡。
3月22日傍晚,湖北宜昌漁民楊江龍解開岸邊的纜繩,啟動漁船,重復他已經重復了30多年的動作,這是他在4月1日禁漁期之前的*后一次收網。
楊江龍的生活并未趕上宜昌的發展速度。靠江吃飯的楊江龍漸漸感受到生活的壓力,因為江里快沒魚了。
沿江而下,千里之外,長江上海寶山水域,是常州漁船的主要捕撈區。一次潮水后,其中一艘收網,卻沒有捕到一尾
比起刀魚來,長江三鮮的另外兩種——鰣魚和
不僅僅是產量,魚種也在持續減少。
一群孤獨的研究者正在與時間賽跑,嘗試使用各種手段延緩長江魚類消失的步伐,保存物種的遺傳物質。
早報記者 黃志強 李云芳 仇鋒平
漁民楊江龍的生活并未趕上宜昌的發展速度。
宜昌地處長江中上游接合部,是湖北的省域副中心城市,近年來經濟發展勢頭迅猛。
47歲的楊江龍三代都是漁民,12歲時他開始跟隨父親在長江上打魚,此后進入專業捕撈大隊,自己不僅有了固定單位,養家糊口吃穿不愁,而且每日為這個城市供應鮮美的長江魚。好景不長,上世紀末,捕撈大隊改制解散,漁民失去了靠山,轉為個體專業漁民,開始獨自在長江上自給自足。靠江吃飯的楊江龍漸漸感受到生活的壓力,因為長江里快沒魚了。
3月22日傍晚,楊江龍解開岸邊的纜繩,啟動漁船。他此行的目的地是萬里長江**壩——葛洲壩水電站。葛洲壩就在宜昌市區,世界*大的三峽水電站僅離該市中心區38公里。
刀魚故事
對于刀魚的未來,水產批發商姚四九有些悲觀,認為刀魚也將步鰣魚和河豚的后塵,“估計五年內就會沒了”。
沿江而下,千里之外,長江上海寶山水域,是常州漁船的主要捕撈區。
一次潮水后,其中一艘收網,卻沒有捕到一尾刀魚。五十多歲的船老大吳風朝上游咒罵,卻又無可奈何。僅僅三五年前,這都是難以想象的事情,旺季里一次潮水能捕五六十斤刀魚。
吳風記得刀魚曾是尋常百姓家常菜,上世紀90年代也才賣幾十元一斤。后來,江水沒那么湍急了,水質也變差了,刀魚也就越來越少了。近年刀魚產量銳減,價格暴漲,而因為中央提倡節約,今年起需求萎縮,價格大跌,3月中旬常州批發價約2000元/斤,僅去年同期1/3。
安徽銅陵市大通鎮的熊根榮也仍能記起十幾年前捕撈刀魚的盛況,“一網下去就是十幾斤,平均一條1兩以上。且捕撈時間也長,可以捕一個半月之久”,捕得沒魚才歇網。說起這兩年的捕撈產量,熊根榮表情暗淡起來,“不怎么樣,總共只搞了六七斤,還虧本。”他說,刀魚的個頭也很小,“平均2條才一兩”。
51歲的熊根榮是“十幾歲就開始搞魚” 的專業漁民,如今雖已上岸居住,但仍靠打魚為生。
當早報記者詢問現在捕撈量是否少了一半時,他立即說道,“不止,少了有七成以上。”
“以上!”他又重復強調。
刀魚和鰣魚、河豚并稱長江三鮮。數十年來,它們在長江里或消亡或銳減,折射出的是整個長江的
因為刀魚是江海洄游魚類,每年2-4月都會洄游到長江里產卵。熊根榮以前甚至還到江蘇去捕撈,因為那里靠近長江入海口,刀魚洄游時**抵達。但熊根榮現在已經不去江蘇了,因為那里的刀魚也少了,“我們網具又小,捕不起來。”
即使這樣,也已經是刀魚限制捕撈十年的結果了。
從2002年開始,長江刀魚實行特許捕撈制度。以銅陵為例,捕撈時間限定為4月27日至5月26日,今年只發放了38張特許捕撈證。銅陵市200多條漁船中,只有38條漁船允許捕撈刀魚。但由于刀魚數量銳減,很多漁民覺得捕撈刀魚還無法平衡柴油等成本,一個月的時間根本用不完,去年熊根榮就只捕撈了3天。
比起刀魚來,長江三鮮的另外兩種——鰣魚和河豚的境遇更尷尬。如今,漁民在長江里已捕不到這兩種魚。
在長江邊上從事水產收購批發生意已逾三十年的姚四九說,長江里已經沒有鰣魚和河豚了。
姚四九記得,鰣魚和河豚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價格都遠貴于刀魚。在上世紀70年代,鰣魚8元/斤,河豚30-40元/斤,而刀魚一斤才1元多。到了上世紀80年代,鰣魚突然捕不到了;到了上世紀90年代,河豚也捕不到了。
熊根榮的記憶也佐證著姚四九的說法。他說,1985年以前還有鰣魚,之后就沒見過。到90年代,河豚也幾乎見不到了。
鰣魚和河豚“消亡”后,刀魚的捕獲量急遽下行。
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淡水漁業研究中心的一組數據說明了整個長江刀魚的總體捕獲情況:1973年長江沿岸江刀產量為3750噸,1983年為370噸左右,2002年的產量已不足百噸。
對于刀魚的未來,姚四九有些悲觀,認為也將步鰣魚和河豚的后塵,“估計刀魚五年內就會沒了”。
葛洲壩下
為了葛洲壩的安全,武警在大壩前劃定了禁漁區,而這個區域恰恰又是目前**能捕到魚的地方。
楊江龍的木船抵達葛洲壩下時,10余條類似的漁船散落在一塊狹小的江面,漁民靠在船上聊著天等待夜幕降臨。這些漁民當初都屬于一個捕魚大隊,解散后依然在一起打魚,每條船上大多是夫妻檔,也有少數父子檔,年近五十的楊江龍是這里*為年輕的漁民,年老的已經超過70歲。
為了保衛葛洲壩的安全,武警在大壩前劃定了警戒區域,禁止漁民進入捕魚,而這個區域恰恰又是目前**能捕到魚的地方,“越靠近大壩越有資源,但又越危險,否則什么魚也捕不到,大壩、防浪墻和航道的建設,改變了河床和水流,只有這點區域有魚類活動,并且水流輕緩適合打魚。”楊江龍無奈地說道。
“這不是拍電視劇,是我們每天都要面對的現實。”楊江龍說,如果貿然作業,武警將剪去充當浮標的泡沫,撒在水下的漁網就被沖得無影無蹤,損失漁具對于這些勉強度日的漁民來說,意味著入不敷出。漁民只能等到武警“松懈”的時候撒網,久而久之便養成了夜間作業的習慣。
1981年1月4日,葛洲壩截流成功,長江被攔腰截斷。一些長江精靈的生命也在此處畫上了休止符。
那一年,楊江龍剛15歲,對家門口的大壩充滿了自豪,雖然捕魚的作業面積有所縮減,但面對豐饒的長江,這并不是什么大問題。
然而截流那年的下半年,他看到了一些不正常的現象。
一群又一群大魚聚集在葛洲壩前游弋,它們大多七八百斤,甚至超過千斤,不顧泄洪閘飛奔而下的驚濤駭浪,一次次奮力前沖,試圖沖破大壩的阻攔,它們有的碰撞得頭破血流,遍體鱗傷,有的則慘死在飛速旋轉的電機葉輪下,楊江龍至今對此記憶猶新。
這些大魚中大部分是中華鱘。中華鱘是一種大型的洄游性魚類,是中國特有的古老珍稀魚類。它與早已滅絕的恐龍生活在同一時代,距今有一億四千萬年的歷史,被譽為“活化石”、“長江魚王”、“水中熊貓”。
截流使沿江回溯的中華鱘無法繼續前行,曾經在長江上游金沙江段的10多處產卵場全部消失,“長江魚王”上億年的腳步不得不止于壩下。
截流后的幾年,每年同一時候,中華鱘依舊會返回宜昌,頑強的它們就在葛洲壩下找到了新的產卵點,物種得以延續,但數量開始急劇下降,成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之后又進入瀕危動物名單。
為救護中華鱘等長江珍稀野生動物,1982年4月,葛洲壩集團成立了中華鱘研究所,主要研究中華鱘的人工繁殖,培育魚苗放流長江。此后,中華鱘新的產卵點也被劃為“長江宜昌段中華鱘自然保護區”,以保障中華鱘*后庇護所的安全。
白鱘情結
白鱘沒有它的“親戚”中華鱘那樣幸運,24歲的楊明和其同齡人只能看到白鱘的標本。
楊江龍的兒子楊明出生在葛洲壩建成后,在長江上長大,今年24歲。
楊明也有遺憾。父親告訴他,自己曾在長江里捕獲過一種和中華鱘一樣大,白色的皮膚,嘴巴很長很尖的大魚,如果還能再捕到了一定給他看,但這個愿望至今沒有實現。楊江龍所說的這種魚名叫白鱘,又稱作中華匙吻鱘,是*大的淡水魚類,和中華鱘一樣,它同樣是與恐龍同時代的物種,僅在中國的長江存活了下來,比大熊貓還珍貴。白鱘因其口吻長達身體的一半,所以俗稱“象魚”、“槍魚”和“劍魚”。
白鱘沒有它的“親戚”中華鱘那樣幸運。中華鱘研究所總工程師肖慧告訴早報記者,葛洲壩建設之初,白鱘還是常見的經濟魚類,在大壩附近一網下去能撈到幾條,但自2003年以來,再也未見白鱘蹤跡,“連人工繁殖的機會都沒有了”。如今,楊明和其同齡人只能看到白鱘標本。
同樣不幸的長江精靈還有白鱀豚。大約2000萬年前,被譽為“長江女神”的白鱀豚離開海洋進入長江,并在中國長江的中下游扎根。2002年7月14日,世界**人工飼養的白鱀豚“淇淇”離世,曾讓整個中國悲傷不已。
據調查,在1980年代初,白鱀豚的種群數量尚有約400頭,1980年至1986年的調查結果是約為300頭,到了1990年約為200頭,1994年以后就不足100頭了。1997年,由農業部發起了長江白鱀豚、江豚同步觀測行動,50多艘中國漁政船在長江中下游進行了為期7天的觀測,*后確認觀測到13頭。2003年,中科院水生所再次進行江上觀測,但未發現一頭。**白鱀豚研究專家、南京師范大學周開亞教授認為亂捕亂撈和航運等人類活動,加快了白鱀豚種群滅絕的速度。專家普遍認為白鱀豚*可能已經滅絕。
三峽阻隔
目前長江“四大家魚”從占漁獲物的80%降至14%,產卵量僅為原來的3%,也將淪為“珍稀動物”。
在楊江龍眼里,葛洲壩攔住了大魚,卻沒有阻隔江水,而三峽工程改變了一切。
三峽工程位于葛洲壩上游38公里處,是世界上*大的水電站,大壩壩頂總長3035米,壩高185米,被稱為長江中的長城。2003年,三峽大壩開始蓄水,長江水文環境發生顯著變化,魚類資源持續衰退,“四大家魚”的產卵繁殖受到直接影響。
生活在長江中的鰱魚、鳙魚、草魚和青魚被稱為長江“四大家魚”,是長江流域市民餐桌上的主要淡水魚類。相關研究表明,“四大家魚”對環境要求嚴格,其產卵繁殖要在適宜的水溫、水流狀態中完成,產卵需要河道水流漲水的刺激,但在產卵高峰的5、6月,天然情況下產生的小洪峰過程,可能因三峽發電而被調平,因而喪失產卵條件。
官方資料顯示,目前長江“四大家魚”從占漁獲物的80%降至目前的14%,產卵量也從300億尾降至目前不足10億尾,僅為原來的3%,也將淪為“珍稀動物”。
在三峽庫區萬州,一些漁民已經不再出江打魚,他們大多已上岸干零活維持家用,漁船只是他們在水上的家,而一些仍在堅持的漁民告訴記者,他們現在不是“魚”民,而是“蝦”民,如今能捕到的只有零星的小蝦和成堆的垃圾。
《長江三峽工程生態與環境監測系統報告》顯示:2004年萬州江段天然捕撈量107噸,日均單船產量1.28公斤,分別為蓄水前2002年的32%和28%,兩大數據均急劇下降。已經退休的長江漁業資源與環境監測萬州監測站站長楊如恒介紹稱,三峽蓄水后,大多數魚類世代產卵繁殖和生長棲息場所發生變化,庫區魚類資源和種群結構正發生嬗變。
漁民隱憂
常州新農水產村書記說,漁民收入之所以沒有降低,是因為魚產量減少后,價格在逐年攀升,但是魚價總不會無限上漲。
春江水暖鴨先知,長江上的漁民*能感知江魚的命運。楊江龍捕撈上岸的魚越來越少了。上世紀90年代,他每天能撈上上百斤魚,“江邊釣魚的人都能輕松釣到幾十斤”,而現在一網下去能有三五條已屬幸運,每天的捕撈量也不過數斤。
從小打魚、如今剛改行賣魚的洞庭湖漁民劉官保回憶起從前,不住感慨,現在魚沒有以前“厚”了,“現在就是打一年,也當不得原來一個月。”湖北石首漁民廖大伯用語更夸張些,“現在長江里沒魚了”。
劉官保和廖大伯都是老漁民,他們的說法代表著很多漁民的心聲。早報記者在走訪湖北宜昌、石首,湖南岳陽,安徽銅陵、安慶,江蘇常州等多地,詢問多名漁民、魚販,幾乎都有類似的感慨。
新農水產村是常州*大的漁村,也是常州現存僅有的兩個漁村之一。目前正是他們捕撈刀魚的季節,可漁民遇上了小年。如在寶山水域,一艘船一次潮水一般只能捕獲2-6尾刀魚。老漁民很難接受這樣的落差,僅僅幾年前,一次潮水還能撈上來幾十斤刀魚,其中不少是2兩半左右的大刀魚。
“漁民收入之所以沒有降低,是因為魚的產量減少后,價格在逐年攀升。”村書記梁林坤說。但是未來呢——魚價總不會無限上漲,也不會總能彌補產量下滑造成的損失吧?
江蘇省淡水水產研究所在長江放置專門的漁網以監測魚產量變化等情況,除去禁捕期,2008-2012年,捕獲量分別為9.6噸、15.4噸、11.3噸、9噸多和7噸多,除2009年有所增加外,近年處于持續大幅減少中。
《長江保護與發展報告2011》顯示,上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長江中下游捕撈量占全國的60%~65%,年均捕撈量從20×104噸迅速增長到150×104噸,年均增長近6.5×104噸;上世紀90年代末至今,產量平穩波動,說明上升勢頭減緩,資源可持續發展受到威脅。另據長江水產所統計,1997-2008年,長江干流青、草、鰱、鳙魚四大家魚魚苗量從35.87億尾波動性銳減至1.81億尾,2007年*低、為0.89億尾。表明水環境在逐步變差,魚苗難以成長,或在個體很小時便被捕獲,導致成魚大量減少。
與時間賽跑
一群孤獨的研究者嘗試使用各種手段延緩長江魚類消失的步伐,但仍憂心魚類消失得太快,連魚種也留不住。
不僅僅是產量,魚種也在持續減少。長江是我國重要的水生生物基因庫和生物多樣性*典型的河流,歷史上有記載的長江水生生物有1100多種,其中魚類370多種。
因缺乏經費、工程量大等原因,近年一直沒能有機構從事基礎研究,確切掌握長江現存的魚種數量,只能通過一些側面進行了解,比如2000年國家公布的《國家重點保護水生野生動物名錄》的保護物種中長江的品種(包括中華鱘、長江鱘、白鱘、白鱀豚、江豚、胭脂魚等是1988年版《名錄》的兩倍。一些重要的珍稀、瀕危水生野生動物如白鱀豚、白鱘、鰣魚等已經或瀕臨絕跡。
一群孤獨的研究者正在與時間賽跑,嘗試使用各種手段延緩長江魚類消失的步伐,保存物種的遺傳物質。江蘇省淡水水產研究所的水生動物精子庫建于2006年,目前存有刀魚、大閘蟹等19種水生動物的精子。全國約有6家水產研究單位存有精子庫,每個精子庫保存的種類從十幾種到三十多種不等,不到我國淡水和海水魚類的百分之一,研究者時常感嘆“為時已晚”,魚類消失得太快,連魚種也留不住。
長江漁民也正在消失。目前長江約有近4萬艘漁船,14萬余專業漁民,他們靠江生活,以水為生,而如今,下水無魚,上岸無地。楊江龍說他每天都盼望上岸,但放不下水中的全部家當,又沒有其他的生活技能,于是只能將后代送到岸上,“這一江水已經養育不了我們的下一代,我們是*后一代漁民”。
楊江龍喜歡教兒子分辨各種長江魚,從小就帶著他在長江上遨游,“我掌舵,我爸在前面指揮,那時候我的個子還沒有橫桿高”,楊明覺得那時候的長江熱鬧非凡,“就像農民秋收的時候,但這個場景已經看不到了”。楊明說自己平日忙于上學、工作,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去江上。
三代打魚的楊家止于楊明,父親楊江龍也感覺到了該告別的時候,但又心存依戀,“從正月初六到現在40多天,我們只捕到了5條像樣的魚,也許等真的沒了魚的時候,只有放棄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百檢能給您帶來哪些改變?
1、檢測行業全覆蓋,滿足不同的檢測;
2、實驗室全覆蓋,就近分配本地化檢測;
3、工程師一對一服務,讓檢測更精準;
4、免費初檢,初檢不收取檢測費用;
5、自助下單 快遞免費上門取樣;
6、周期短,費用低,服務周到;
7、擁有CMA、CNAS、CAL等權威資質;
8、檢測報告權威有效、中國通用;
客戶案例展示
相關商品
版權與免責聲明
①本網注名來源于“互聯網”的所有作品,版權歸原作者或者來源機構所有,如果有涉及作品內容、版權等問題,請在作品發表之日起一個月內與本網聯系,聯系郵箱service@baijiantest.com,否則視為默認百檢網有權進行轉載。
②本網注名來源于“百檢網”的所有作品,版權歸百檢網所有,未經本網授權不得轉載、摘編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想要轉載本網作品,請聯系:service@baijiantest.com。已獲本網授權的作品,應在授權范圍內使用,并注明"來源:百檢網"。違者本網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③本網所載作品僅代表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百檢立場,用戶需作出獨立判斷,如有異議或投訴,請聯系service@baijiantest.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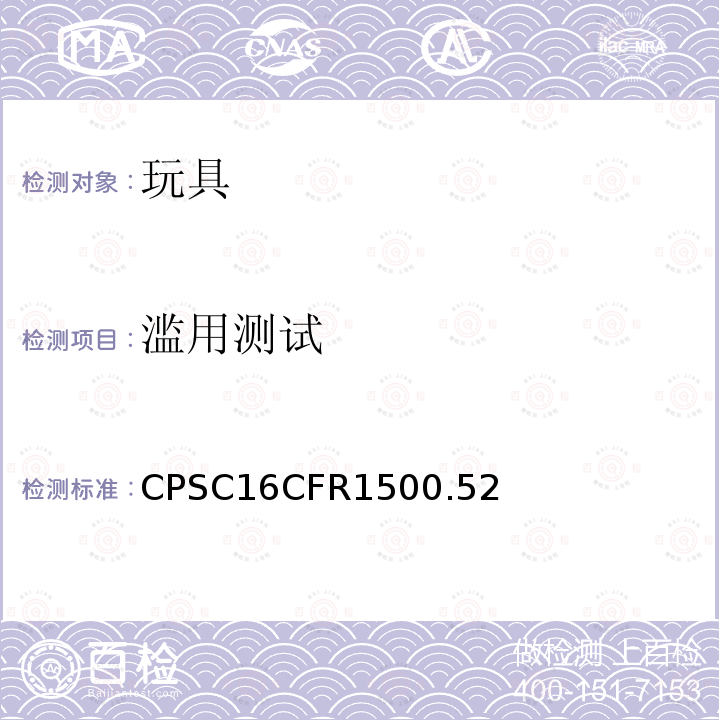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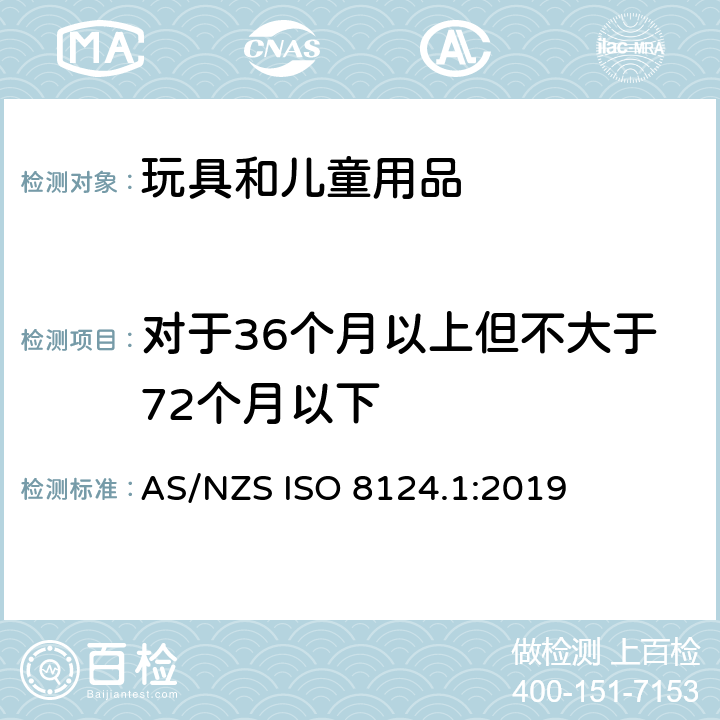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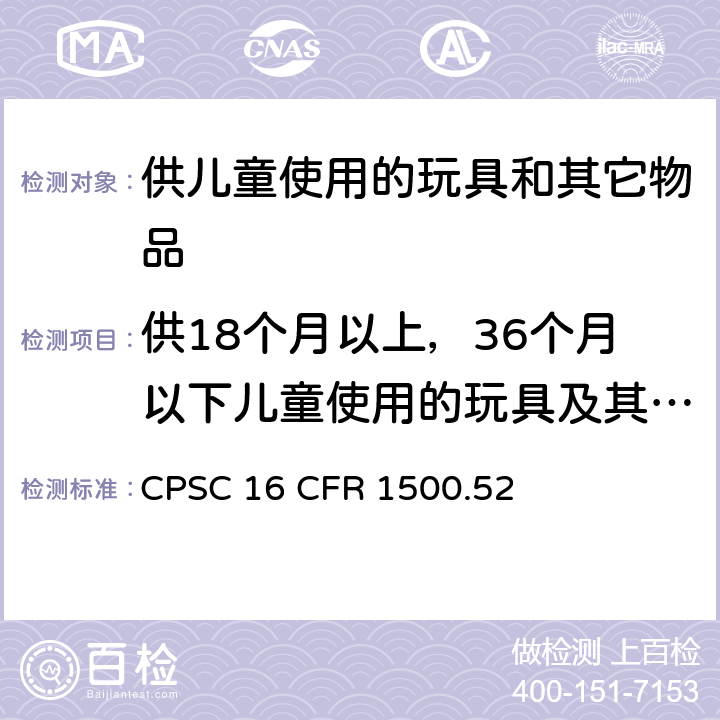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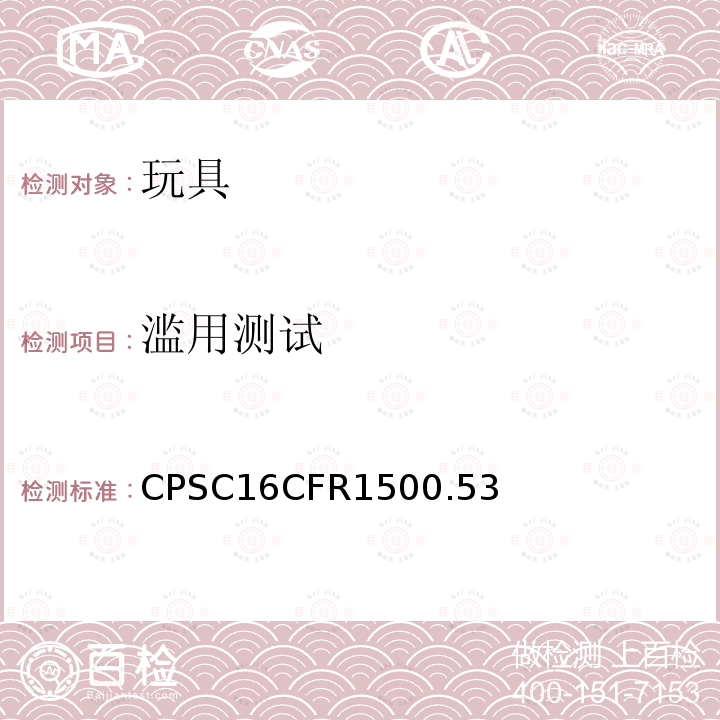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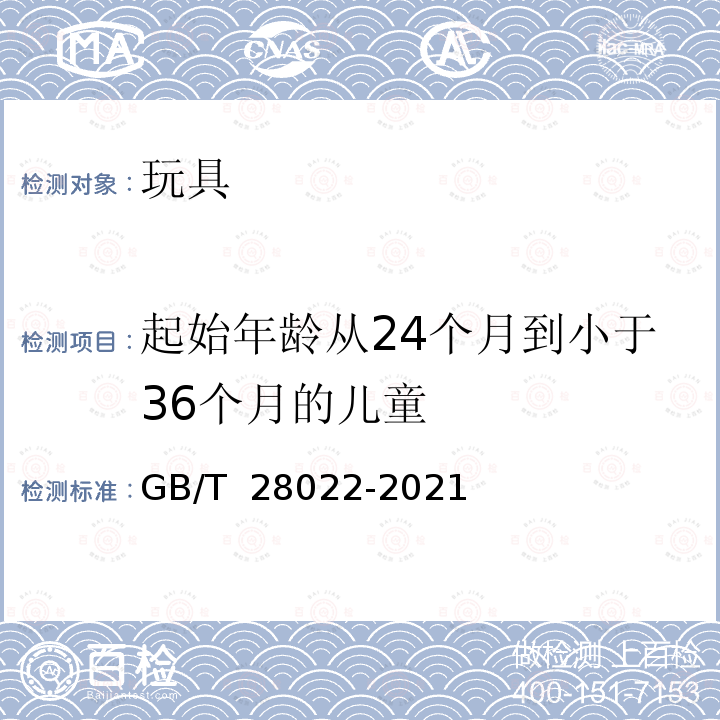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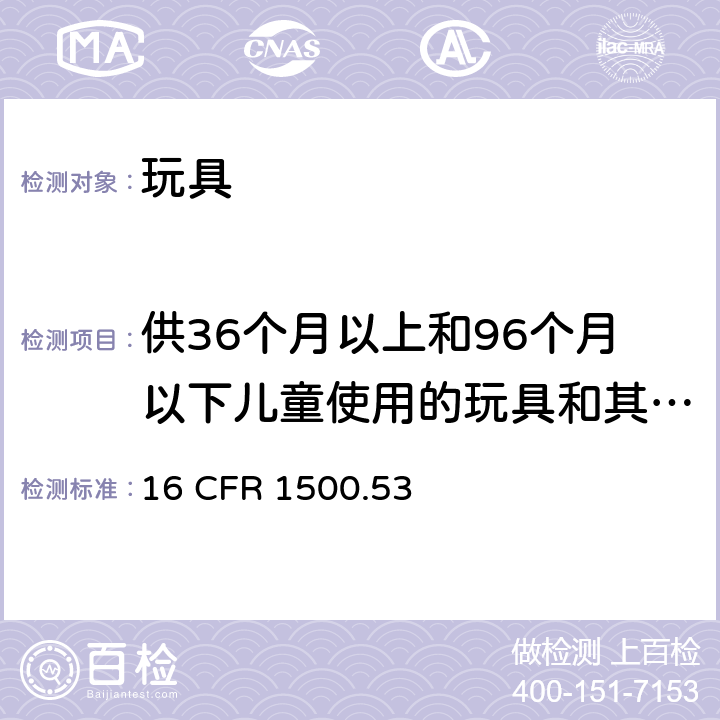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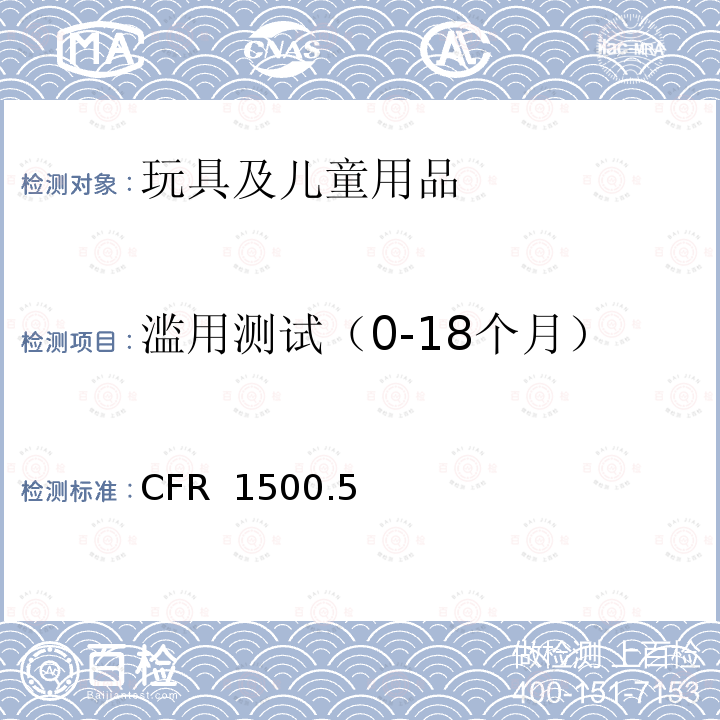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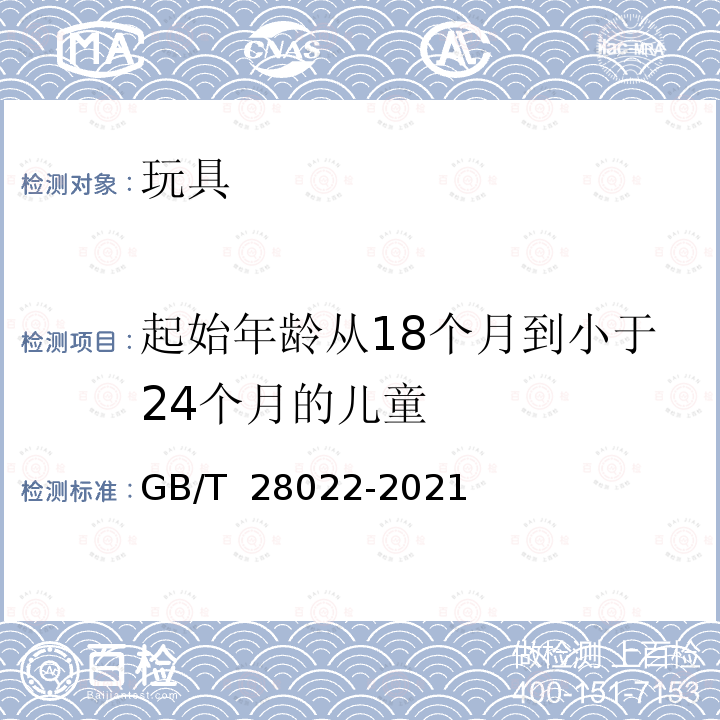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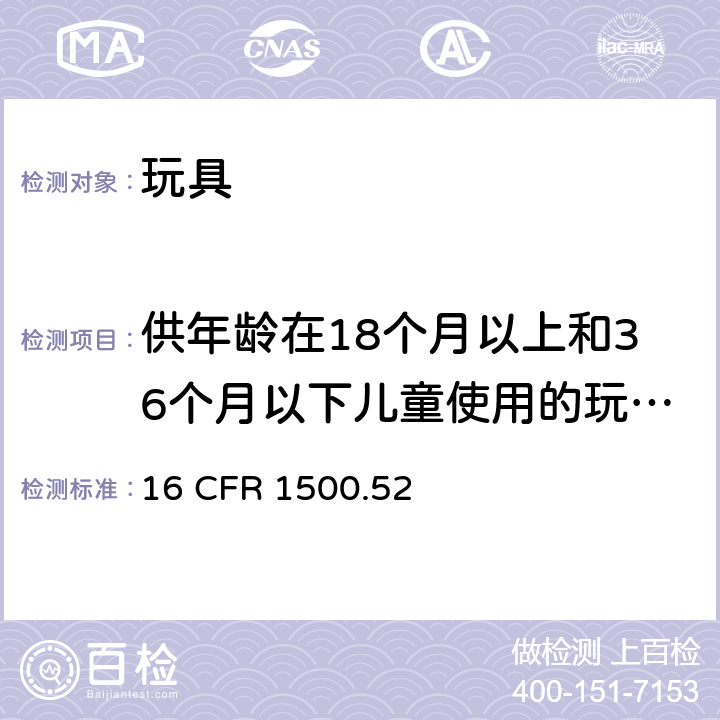










 400-101-7153
400-101-7153 15201733840
152017338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