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重現”國寶素紗禪衣仿制品僅49.5克與真品無限接近
作者:百檢網 時間:2021-12-07 來源:互聯網
仿制品素紗襌衣(上)與真品進行對比。
織造
“這件素紗襌衣,我一邊織就在一邊想,古人的智慧真是太偉大了,他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57歲的楊建順頭發花白,在南京云錦研究所的一臺純手工木質織機上用兩個木梭子來回拉著絲線,每拉一下,就輕輕地踩一腳織機的經線木棍,接著拿打緯木刀排緊緯線。梭子上綁的蠶絲只有1/3根頭發絲粗細,這讓楊建順每次紡織都要戴上老花鏡。
就在這臺織機上,研究所的團隊歷時兩年時間終于成功仿制出重量約49克、目前世上*輕*薄的素紗襌衣。曾經,國寶素紗襌衣的仿制是世界性難題,近日,南京云景研究所的仿制團隊成員向廣州日報記者介紹了他們仿制素紗襌衣的幕后故事。
南京云錦研究所門外,碩大的牌樓正中懸掛著“江寧織造”的鍍金匾額,云錦是元明清三朝的皇家貢品,一直保留著傳統的提花木機織造,技藝至今無法用現代機器來替代。2009年,云錦被評為聯合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皇家御用、世界非遺等元素,讓云錦成了仿制國寶素紗襌衣的不二之選。
2017年,南京云錦研究所在競爭激烈的湖南省博物館(簡稱“湘博”)仿制素紗襌衣等文物的投標中勝出,團隊仿制素紗襌衣的故事就此拉開序幕。
花5倍價格收集“老弱病蠶”
自152 0173 3840年在長沙市馬王堆漢墓發掘出土,素紗襌衣的仿制就一直是現代紡織業的難題。這件目前世界上*輕*薄的衣服,衣長128厘米,通袖長190厘米,素紗絲縷*細,重僅49克。
多年以前,國內多家機構都曾嘗試仿制,但*后的結果都是仿制品遠遠超過真品重量。而真品因為長期展出,光線、空氣正對其造成很大的損害,這讓仿制素紗襌衣迫在眉睫。
此次項目的負責人、南京云錦研究所設計中心的工藝美術大師楊冀元告訴記者,之前仿制失敗,原因是蠶絲質量太重,現代蠶絲的纖維細度*低也有16旦,而經過檢測,素紗襌衣的纖維密度能達到11旦。因為古代蠶吐絲更細,質量也更輕。
“我們現在的‘蠶寶寶’是四眠蠶,就是蠶在幼蟲期4次停止食桑就眠蛻皮所形成的蠶繭,這種蠶繭比古代的蠶繭要粗很多。所以,我們必須找到更細的蠶絲。早在2016年,我們就開始聯系江浙滬的繅絲廠,讓他們專門提供三眠蠶或比較瘦弱的病蠶,這就像尋找蠶中發育不良的‘早產兒’一樣。”楊冀元告訴記者,為了仿制素紗襌衣,團隊用了高于常規蠶絲5倍的價格,專門收購“老弱病蠶”。
仿制品幾可以假亂真
后來,隨著與湘博正式達成協議,楊冀元等團隊成員來到長沙,對素紗襌衣的真品進行采樣。
“當時真品就放在玻璃罩子里,罩子只能打開20厘米的小口,我們的工作人員幾乎都是從小口把頭探進去,對真品進行采樣。我們當時用到了各種儀器,比如顯微鏡、組織分析儀,對它的絲織結構進行完整的采樣。”楊冀元說,素紗襌衣的面料顏色不能用色譜分析儀進行分析,他們采用染料和紅茶浸泡相結合的方法,進行面料染色做舊處理,先后染了20多個小樣,再一次次開罩,用肉眼與真品進行對比,力圖顏色和真品無限接近,才確定了*終顏色,“真品太輕太薄了,我們把頭探進去,人的呼吸都能讓面料的表面絲織物飄動,因此每次采樣我們都要花大量時間,這讓我們當時幾乎半個月的時間都住在湘博。”
“我們后期先后做了10件樣衣,不斷與真品的尺寸對比,修改細節,直到*后做出一件大家都非常滿意,和真品無限接近的仿制品。”楊冀元告訴記者,素紗面料質地輕薄,*易破損變形,一般的服裝裁剪中的繪制工具都無法在面料上直接應用;為此,他們先將面料平鋪,用噴壺噴至潮濕拉直,等面料微干時再按制版進行繪制及裁剪,固定面料的同時使裁片更加平整,避了熨燙造成的不穩定形變。
而在*后的縫制過程中,楊冀元根據研究實驗復原了西漢縫制方法,在符合所有制版采樣數據的情況下進行移位縫紉,*終完成與文物現狀一致的素紗單衣仿品。
在經過湘博相關專家的鑒定后,這款重量為49.5克的仿制品得到認可,幾乎到了“以假亂真”的地步。目前仿制品已移交湘博,后期將替代原文物用于博物館內展陳。
天衣無縫純粹靠“手感”
在南京云錦研究所仿制團隊中,楊冀元主要負責仿制品后期的染色、裁剪和成衣的過程。而前期蠶絲紡織的過程則由楊建順和另一位云錦非遺傳承人共同完成。
楊建順說,在購買了足夠的三眠蠶作為原料后,團隊開始專門為素紗襌衣定制織造機。“因為古代織造技術的限制,門幅要比現代織機窄很多,我們采用*傳統的織造方式,專門定制48厘米尺幅寬度的機臺;另外,因為三眠蠶絲過細,現代的鐵梭子過重容易造成拋梭不均,還容易把絲線磨斷,我們又定制了重量較輕的木梭子,以便更好地輔助這種細蠶絲的織造。”
楊建順說,在仿制過程中,機臺必須不斷調整,盡量保持水平,才能讓比頭發還細的蠶絲不斷,“一開始織機沒調整好時,每天要斷100~200根蠶絲,這時我就要看蠶絲的斷點,分析織機的問題所在,整整調試了兩三個月,我們才讓織機達到理想的狀態”。
此外,仿制品的絲織工藝必須和原樣完全一致。楊建順參考了考古報告記載的紋樣內容及電腦測繪紋樣的樣式,力圖1:1還原紋樣,“素紗襌衣的紋樣太特殊了。通常,絲織品的緯線都是一扭到底,但這件衣服的緯線卻是一根順時針扭,另一根逆時針扭。”楊建順說,為了保證紋樣不出錯,所有的絲線都是一紅一白相間隔的,這種細蠶絲幾乎不能用肉眼看到,“紅色的蠶絲是用植物染料染的,我們紡織結束后,用水一洗,顏色就可以洗掉了”。
而這些還不是紡織蠶絲*難的一環。素紗襌衣用的絲織工藝是平紋紗,面料的密度必須控制得非常均勻,既不能過粗,也不能過細,這純粹依托于師傅的手感,“它對織手的要求太高了,經驗豐富、專注力、感覺缺一不可,堪稱百里挑一,一旦開始織造便不能夠隨意替換織手,因為每個師傅手感和力度的不同,都會影響面料的經緯密度和質感”,楊建順告訴記者,他花了將近3個月的時間練習手感,就是為了保證打緯木刀在壓緯線時的力度均勻,“打1cm長的緯線,必須是50梭,多一點少一點都會影響呈現效果。”
“那位做素紗襌衣的古人真是太偉大了,我們花了差不多1年的時間來紡織蠶絲,現在還可以依靠一些先進的儀器,還有老花鏡可以看清絲線,而古代人卻幾乎純依靠手感,讓絲線均勻伏貼,這太不可思議了。”楊建順感慨說。
未來有5件國寶將被仿制
楊冀元說,未來,他們還將復制湘博的另外5件精湛絲織品。“它們分別是羽毛貼花絹、漆纚紗冠、朱紅菱紋羅絲綿袍、印花敷彩紗絲綿袍和一個香枕,這5件絲織品的仿制難度,就是這樣由高到低地排序,甚至會比仿制素紗襌衣還難。”
楊冀元進一步介紹:“羽毛貼花絹同樣出土于馬王堆一號漢墓,是我國出土*早的羽毛畫,層次分明,色彩斑斕,具有強烈的裝飾效果,用來裝飾內棺,象征著為死者披上一件羽衣;漆纚紗冠是辛追夫人的兒子所戴的帽子,給人看起來像鐵絲編的一樣,但實際上它卻是用蠶絲編制的,目前我們制作漆纚紗冠的方法已經研制出來,只要改變蠶絲的組織結構,就能做到帽子的效果,今年年底就能交付;而香枕里塞著佩蘭等香草,也是我國出土*早的成型枕頭……”
他說道,朱紅菱紋羅絲綿袍和印花敷彩紗絲綿袍的面料也正由他進行制作,“目前已經到了收尾階段”。據悉,所有5件文物仿制品,將于2022年年底前全部交付給湖南省博物館。
云錦曾為三朝“皇家御用”
楊建順告訴記者,正是40多年來制作南京云錦的積淀,才讓他有足夠的積淀,得以仿制難度*高的素紗襌衣。他是1978年從事南京云錦織造工作的,師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云錦織造老藝人王長金、王杏榮等人。
楊建順說,南京云錦曾是元明清三朝的皇家貢品,織工按要求編織成型后,統一由江寧織造府分門別類送至內廷,“云錦不僅可以做衣服,還可以用于貼窗花、做圣旨的貼布,是皇家御用。為了保證技藝不外傳,歷代都是傳男不傳女,當然,現在早已經突破男女的限制了”。
楊建順說,新中國成立后,曾經皇家御用的云錦“飛入尋常百姓家”,做云錦的老師傅進入南京的幾個合作社工作。1978年開始,年僅16歲的楊建順跟著師傅苦練,直到6年多后才出師。此后,他參加了定陵博物院妝花緞龍袍、織金奔兔紗、喜字并蒂蓮、日本琉球王袍等紡織物的研制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培養了許多年輕人。
“我們研究所此前已經承接國內很多博物館要求仿制古代紡織品的業務,比如萬歷皇帝的龍袍等。”楊建順說,素紗襌衣的織造工藝和云錦雖然有所不同,但正是多年制作云錦的經驗讓他“一點就通”。
他認為,傳統工藝的局限性在銷售中已漸漸凸顯出來,云錦發展需要不斷創新。“創新,除了圖案設計方面,工藝技術也要與時俱進。”
(廣州日報)
百檢能給您帶來哪些改變?
1、檢測行業全覆蓋,滿足不同的檢測;
2、實驗室全覆蓋,就近分配本地化檢測;
3、工程師一對一服務,讓檢測更精準;
4、免費初檢,初檢不收取檢測費用;
5、自助下單 快遞免費上門取樣;
6、周期短,費用低,服務周到;
7、擁有CMA、CNAS、CAL等權威資質;
8、檢測報告權威有效、中國通用;
客戶案例展示
相關資訊

行業熱點
版權與免責聲明
①本網注名來源于“互聯網”的所有作品,版權歸原作者或者來源機構所有,如果有涉及作品內容、版權等問題,請在作品發表之日起一個月內與本網聯系,聯系郵箱service@baijiantest.com,否則視為默認百檢網有權進行轉載。
②本網注名來源于“百檢網”的所有作品,版權歸百檢網所有,未經本網授權不得轉載、摘編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想要轉載本網作品,請聯系:service@baijiantest.com。已獲本網授權的作品,應在授權范圍內使用,并注明"來源:百檢網"。違者本網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③本網所載作品僅代表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百檢立場,用戶需作出獨立判斷,如有異議或投訴,請聯系service@baijiantest.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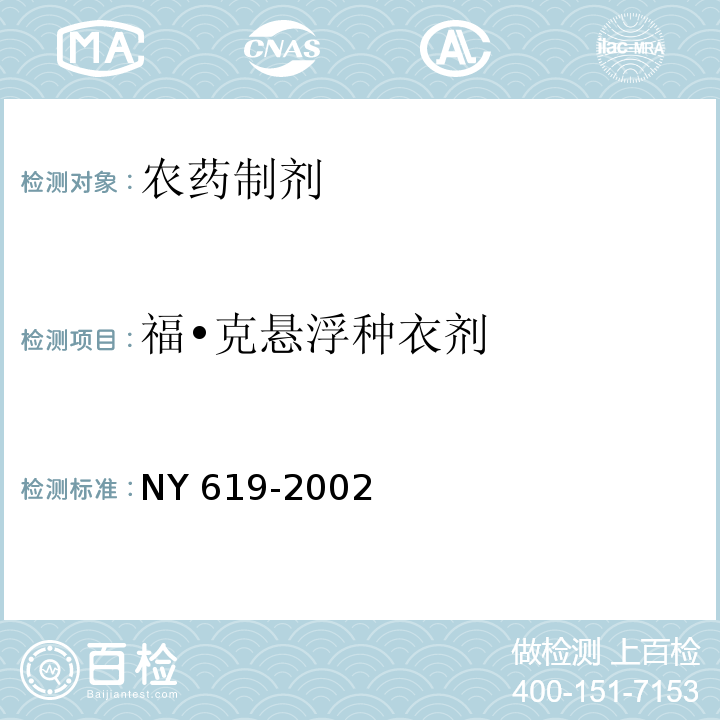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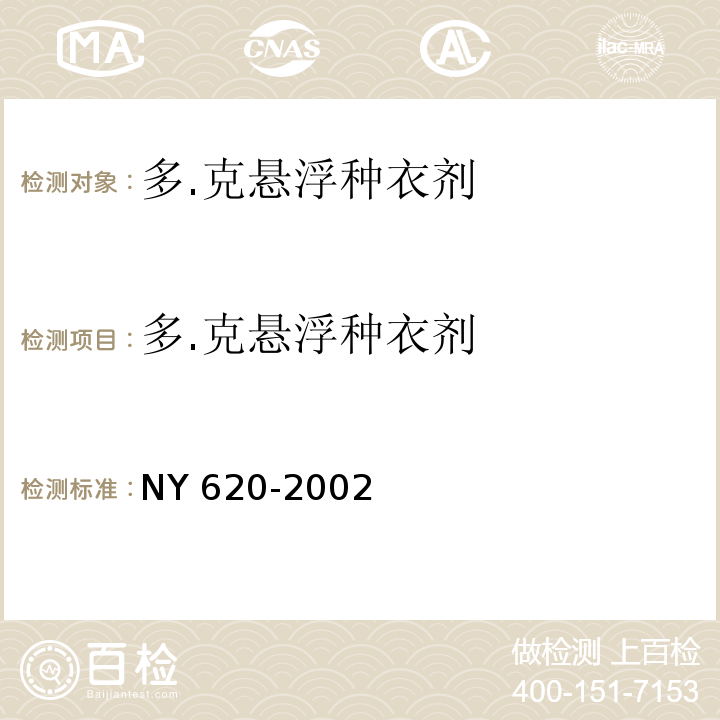








 400-101-7153
400-101-7153 15201733840
152017338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