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記(宋峻梁)
作者:百檢網 時間:2021-12-15 來源:互聯網
棉花記
小學升初中那年,作文的考題就是“棉花的葉子”,費了我好一番腦筋,寫得亂七八糟。后來聽老師講,能寫出“光合作用”,就可以及格,那時感到很奇怪,考作文又不是考生物和自然,為什么非要寫光合作用呢。我記得是從欣賞的角度寫的,少不了對葉脈、顏色的描寫,所以多年后仍然記憶深刻,到現在對那樣的評判方式都覺得可笑。其實,從功能的角度描述棉花的葉子,也可以加入審美,甚至寫得擬人化,這是*容易操作的也是常被使用的方法。無疑,棉花的葉子在整個植株出芽、成長,到凋落的過程中,既擔當著主角,也擔當著配角,從鵝黃到嫩綠,再至蒼綠,再到沾染了夕陽之光的銹紅和枯黃,這也是一生。棉桃就是在許多葉片庇護和鼓勵下,開花坐果,仿佛蠶吃掉所有葉子,*后吐絲般,*后在萬物凋敝時,成為季節*后呈現的花朵。確切說,那不是花朵,而是一個隱喻。平原上的每種植物,都在經歷著相似的成長過程,而只有棉朵,以吐露的方式,呈獻出人間生命的底色。
但是,在畫家嚴超先生的目光里,棉花是開放在鋼鐵般枝椏上的花朵。他審視棉花,也是在審視大地與人類生命的契合之結。鐵銹色的枝椏,暗示了季節下農業的悲壯,暗示了盛開是怎樣一件事。白,就是真理,是歷史*后的總結,白不是空,也不是空白,而是具有質感的,是所有事物的寄托。在平原上,大雪到來之前,該收割的都收割了,黃的玉米,青的白菜,紫的地瓜,紅的辣椒,在這些之后,棉朵還在開裂,在略顯疲憊的陽光下,打開一扇一扇堅硬的門,送出一朵一朵溫柔的棉花,這樣的棉花可以用來比喻母親的溫暖,可以比喻少女的肌膚,可以比喻飄蕩的白云,而對于棉花的禮贊,可以用上所有感恩的詞匯。
棉花的白,是所有的白。
充盈、飽滿的棉朵,仿佛一件鼓鼓囊囊的包裹,傳遞著溫暖的感受,它暗懷的每一枚黑色的棉籽,多像緘默的牙齒。我們看不到它的內部,棉朵秘密的以纖維包裹住種子,每一絲纖維之間存在著秩序,摘取棉朵的手,尊重這種秩序,他不是攫取,而是摘取,對于土地和植物的贈送,或者說藉由勞作而獲取,不必有任何負罪感。對于畫家畫面里的蒼茫,總是一種逼近,后面似乎就是世界,就是歷史,是一個巨大的容器,也是一個粗瓷大碗。
各種白,是一種白。枯葉落盡,細弱而結實的枝椏,仍像一條條手臂,堅實而悲壯,不斷托出一個個白色的棉朵,而托起棉朵的手掌,都有尖銳的手指,以刺的形式,和刀鋒的個性,仿佛打開一尊鎧甲。是投降嗎?顯然不是,是給予,是力盡后的善良,直到初雪覆蓋大地,把整個季節埋葬,它仍然張開著。
棉花,*大的價值在于棉朵,它的白,除此之外,盡皆退去,仿佛英雄與眾生。因為棉花,人性變得復雜了。衣與食,是一個人生存的基線,也是尊嚴的基線,也仿佛就是欲望的開端,從零開始,從空白開始。當大地上的一切盡皆收藏,隨即到來的冬天仿佛就是一個漫漫的長夜。幸好,它的潔白,承接了人們對色彩的想象,它的潔白又是為給人類遮羞而來,作了燈芯,作了布匹,都是在文明的起點處,抻長歷史。
百檢網專注于為第三方檢測機構以及中小微企業搭建互聯網+檢測電商服務平臺,是一個創新模式的檢驗檢測服務網站。百檢網致力于為企業提供便捷、高效的檢測服務,簡化檢測流程,提升檢測服務效率,利用互聯網+檢測電商,為客戶提供多樣化選擇,從根本上降低檢測成本提升時間效率,打破行業壁壘,打造出行業創新的檢測平臺。
百檢能給您帶來哪些改變?
1、檢測行業全覆蓋,滿足不同的檢測;
2、實驗室全覆蓋,就近分配本地化檢測;
3、工程師一對一服務,讓檢測更精準;
4、免費初檢,初檢不收取檢測費用;
5、自助下單 快遞免費上門取樣;
6、周期短,費用低,服務周到;
7、擁有CMA、CNAS、CAL等權威資質;
8、檢測報告權威有效、中國通用;
客戶案例展示
相關商品
相關資訊

暫無相關資訊
行業熱點
版權與免責聲明
①本網注名來源于“互聯網”的所有作品,版權歸原作者或者來源機構所有,如果有涉及作品內容、版權等問題,請在作品發表之日起一個月內與本網聯系,聯系郵箱service@baijiantest.com,否則視為默認百檢網有權進行轉載。
②本網注名來源于“百檢網”的所有作品,版權歸百檢網所有,未經本網授權不得轉載、摘編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想要轉載本網作品,請聯系:service@baijiantest.com。已獲本網授權的作品,應在授權范圍內使用,并注明"來源:百檢網"。違者本網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③本網所載作品僅代表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百檢立場,用戶需作出獨立判斷,如有異議或投訴,請聯系service@baijiantest.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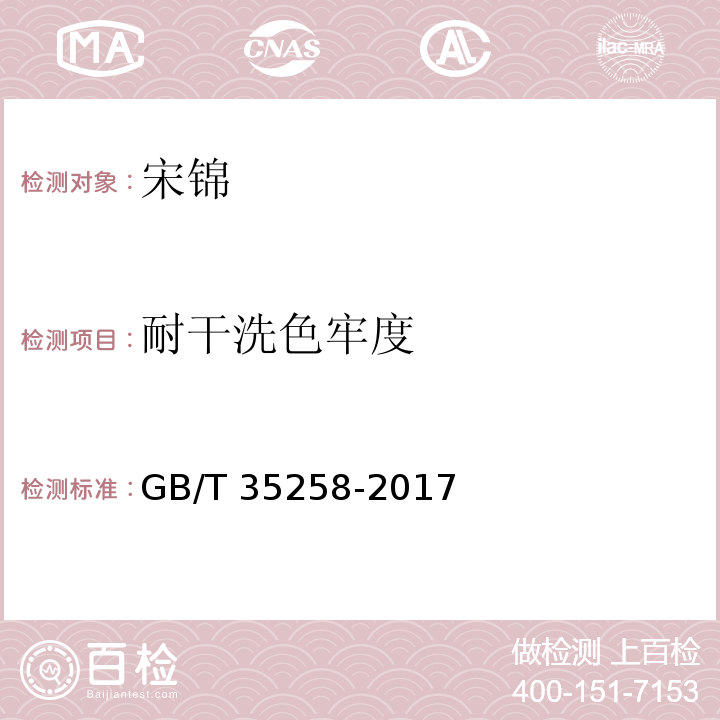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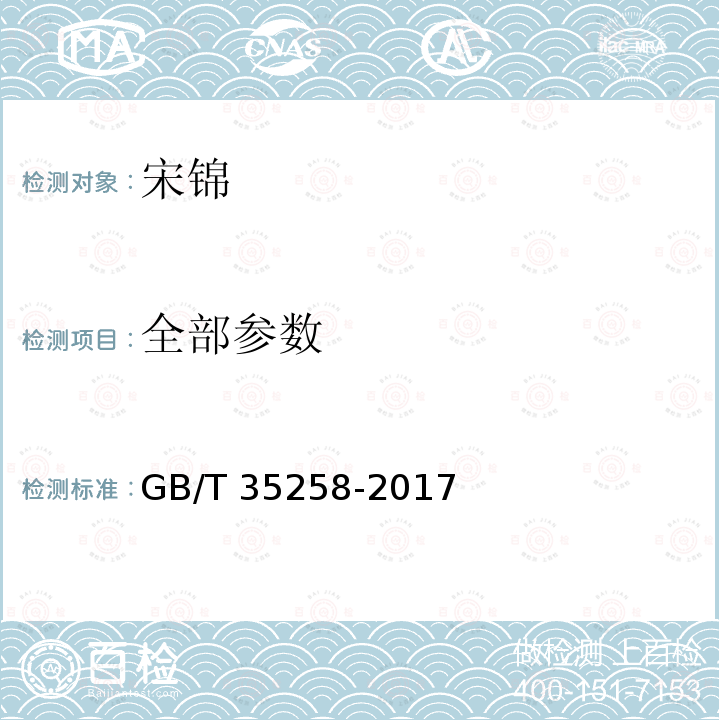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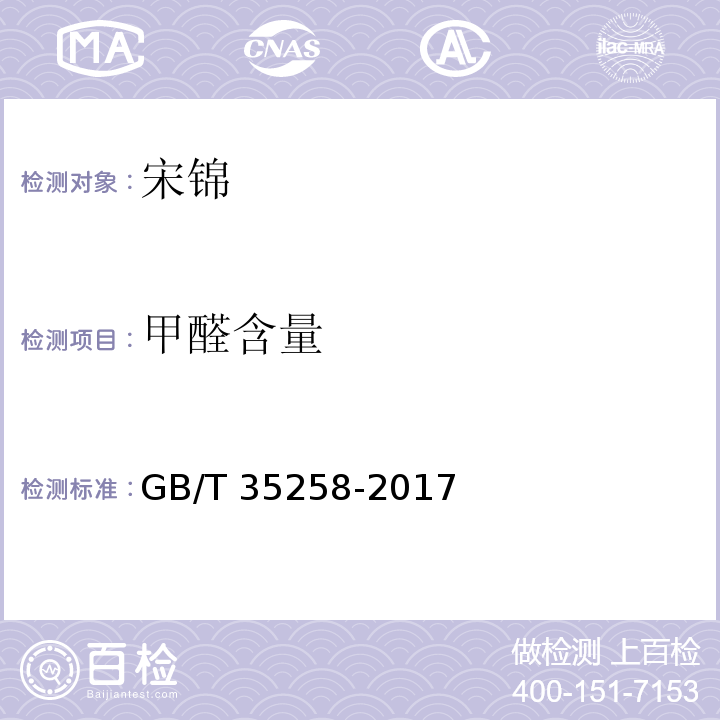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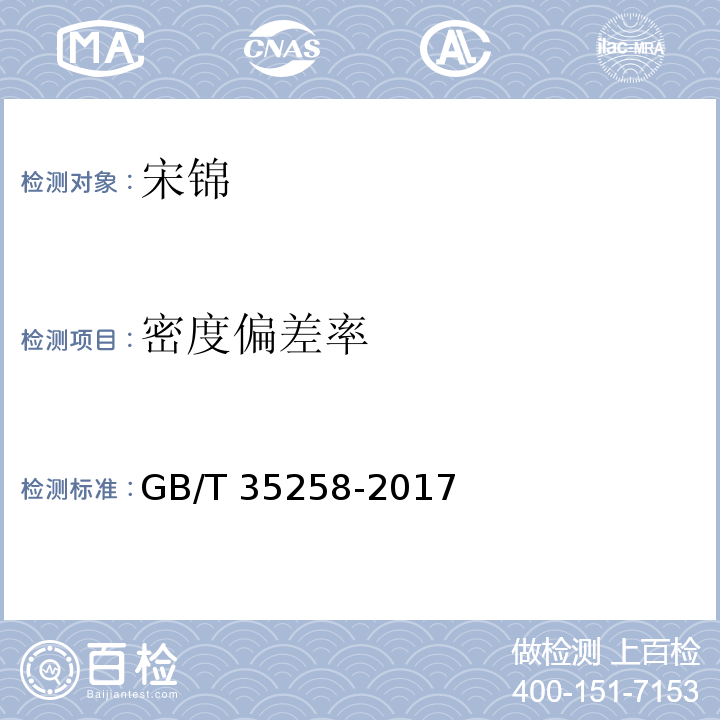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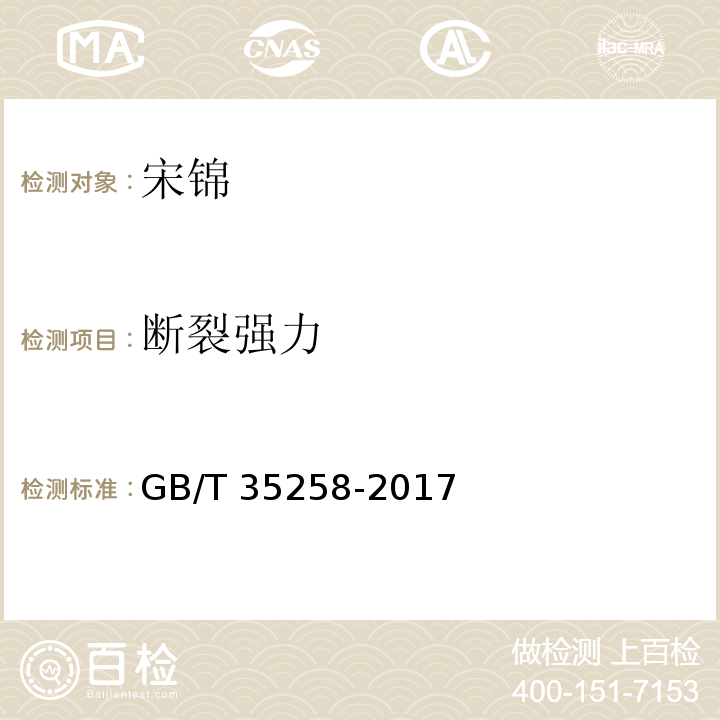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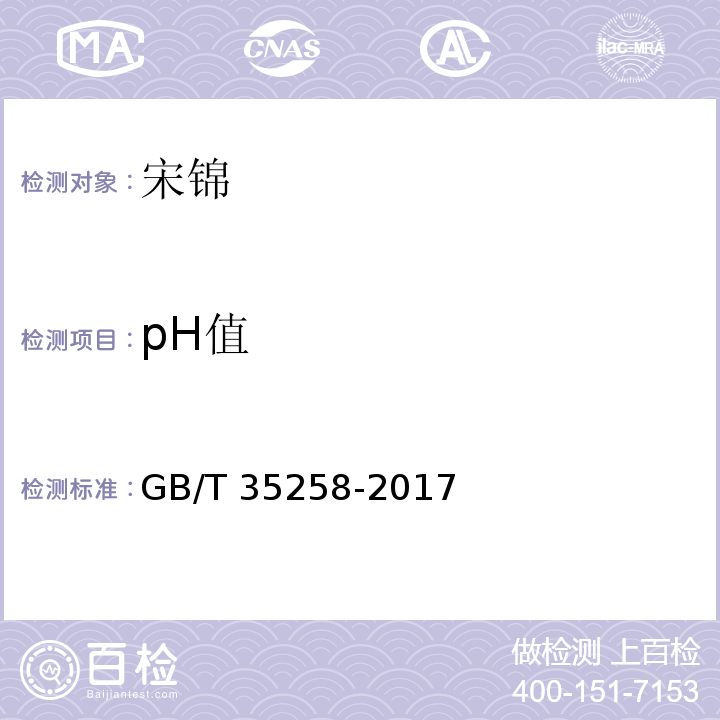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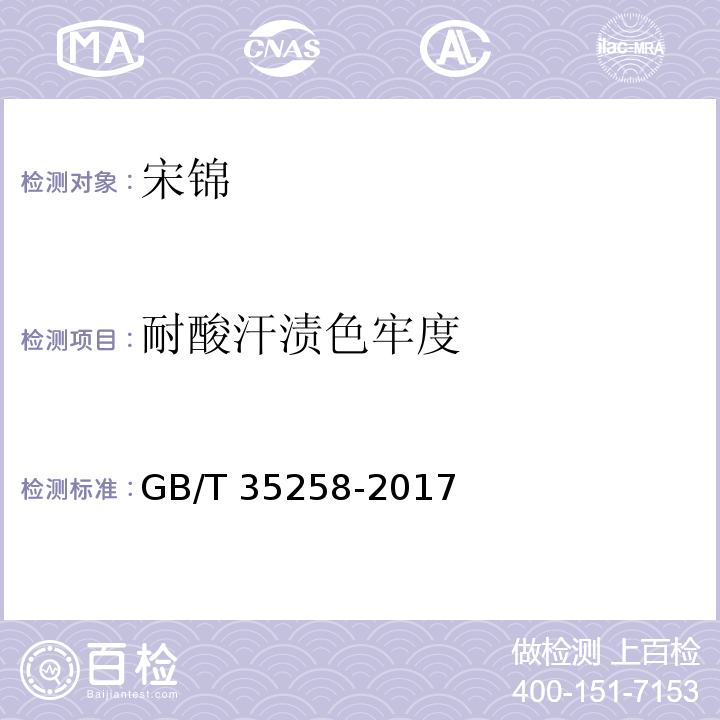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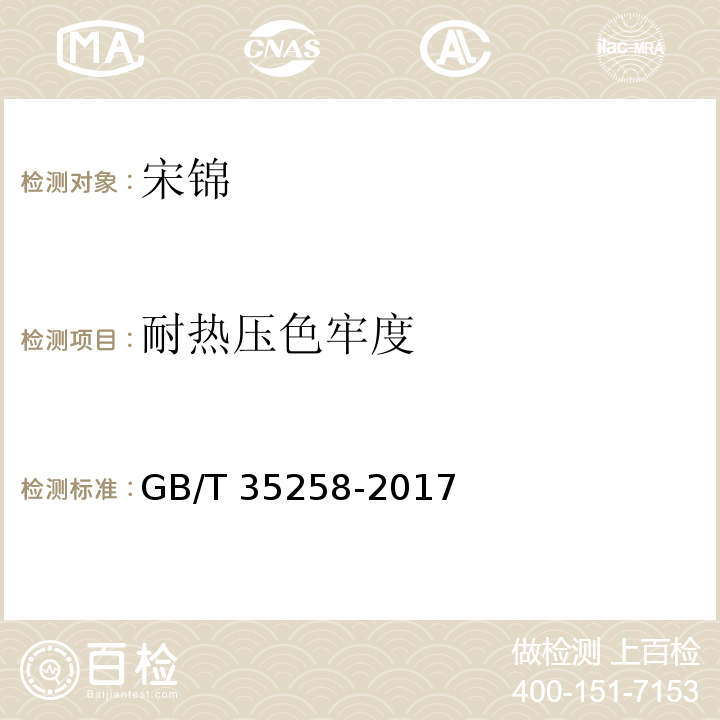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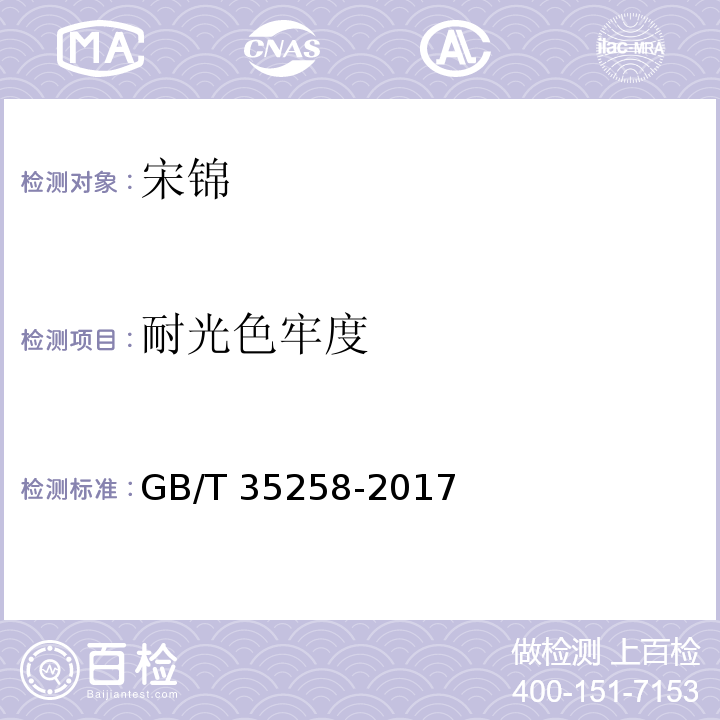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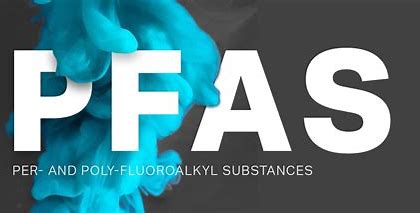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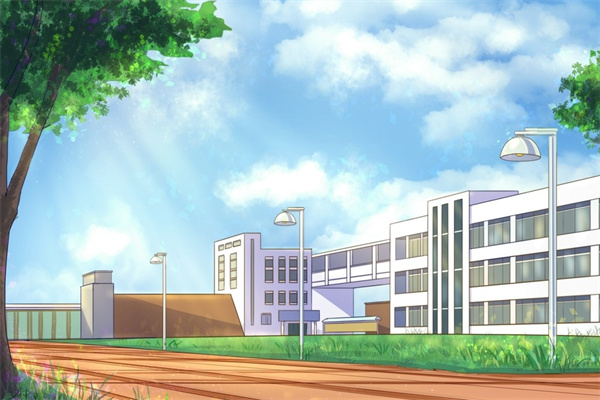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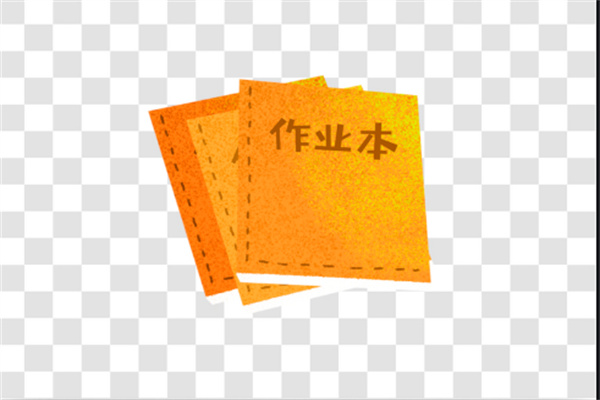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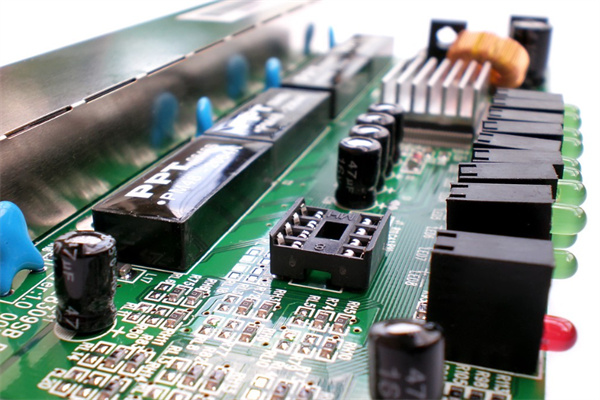




 400-101-7153
400-101-7153 15201733840
152017338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