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江織造產業面臨嚴峻的困境
作者:百檢網 時間:2021-12-07 來源:互聯網
“今天的減,是為了明天更好的加!”上次見到蘇州市吳江區經信委副主任沈斌時,他的這句話就印在了記者腦海。關于吳江區淘汰10萬多臺低端噴水織機的消息一度成為行業焦點話題,引起熱議。前不久,記者有機會走進吳江大廈,再次聽沈斌深度剖析了吳江紡織產業的發展現狀和出路,受益匪淺。
多個“**”卻暗藏危機
正如沈斌所說,沒人可以否定吳江在中國紡織行業發展中的地位。
520萬噸的化纖紡絲生產能力,約占全國產能十分之一,更有恒力集團躋身全球500強;34萬臺織機,年*低產布200億米,可供全國人均15米;如此數量級已經完全顛覆了以往傳統手工業經濟的模式,吳江紡織行業基礎已在。這點從另一方面也能證明——東方絲綢市場,152 0173 3840年10月開始運營,這30年,更直接見證了吳江紡織行業的輝煌:連續多年紡織產量全國**、東方絲綢市場交易額**。
批發市場
中國東方絲綢市場
“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這些‘**’背后也隱藏著危機。”沈斌話鋒一轉說道,這些**都是由原來的粗放經營得來的,整體來看:大而不強、多而不精。“體量是很大,但有些‘虛胖’,數量也不少,但‘專、精、特、新’的不多,導致當前問題越來越凸出。”
沈斌提到,從產業角度來審視,改革開放以來,紡織行業一直在以“攤大餅”的形式粗放發展,可如今,這種模式已經行不通,“面還是那些面,大餅做不了了,那這些面是做餛飩還是餃子?”深入淺出的一問,正是吳江紡織轉型的關鍵所在。
從大的經濟局面來看,以往,緊缺經濟時大部分商品都很暢銷,賣方市場特征明顯,傳統低端產品也不愁銷路,可現在產業進入“天花板”時期,邁入買方市場,消費者對產品質量等各方面需求都提高了,需求差異化也日趨明顯。再看紡織行業,必須承認的是部分紡織企業仍存在“小、散、亂”的情況,前些年有些人用手里的閑錢,買幾臺機器,不講究技術,用做傳統農業的辦法來做工業,也賺到了一些錢,但現在的市場經濟下,這些企業依舊賺錢是不正常的,不賺錢才是正常的。沈斌認為,沒有技術、沒有管理、沒有營銷的模式本就是不符合市場規律的,也自然該被市場淘汰。
曾經在江蘇陽光集團參觀時,有人笑談道,“吳江一車布不抵陽光集團的一匹布”,沈斌承認這是有道理的,因為一方是精益管理,一方則是粗放經營。吳江紡織大量生產基礎布料,卻缺少對面料的深加工。不少行業內人士都曾聽說過“紹興的面料,吳江的里料”“吳江是紹興的白坯市場”,里料自然不如面料值錢,這也難怪有人感慨,“吳江犧牲了環保,卻沒有賺到錢!”以上種種既是產業事實,也是值得反思的地方。
換一種角度,從產業鏈來說,吳江有200億米坯布,卻只有50億米印染,這份不協調是多么明顯的發展瓶頸!再看后道,在吳江幾乎沒有服裝時尚可言,甚至中等或者是特色人群定位的服裝品牌也沒有。
服裝時尚是產業鏈重要的一環
所有癥結都指向了“升級”。
再次細診紡織脈
其實,沈斌對于吳江紡織產業的判斷并非僅僅源于經濟大勢,更有深層原因。
縱觀該地區紡織產業,不難發現有以下幾個明顯特征:**,總體層次偏低,特別是織造環節處在產業鏈價值底端,產品附加值不高;第二,從“十二五”開始,紡織產業整體投資明顯放緩,原來投在化纖、織造的產能已經基本飽和,很難再尋找到新增產能空間,邁入改進需求高峰;第三,效益偏低,從2016年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吳江區畝均稅收可達12.14萬元,而紡織行業只有6.94萬元,低于全區平均水平。其中,化纖14.90萬元、印染13.30萬元、織造4.22萬元,織造行業連畝均稅收值一半都不到。究其原因,大概有兩個:一是終端開票消費較少;二是織造畝均稅收確實偏低。
再從要素層面深入分析,吳江織造產業確實面臨著嚴峻困境:
**,織造產業中部分企業資金供求矛盾凸顯,話語權不足,購買原材料必須現款結算,而產品賣出時又有應收款,甚至部分企業還因擔保造成資金風險,被銀行限貸,此外,還存在庫存導致的產品價格不穩定因素。
第二,勞動力資源緊缺。據調查,目前紡織行業中車間操作工人80%~90%都是外地人,本地人一般更傾向于管理崗位。加之現在的勞動力主力為90后,甚至00后,他們的思想訴求與老一輩不同,選擇工作更注重企業文化、職業發展前景和自我價值的實現,他們寧愿在辦公室少掙一點也不愿意下車間。這也是企業招不到人需要考慮的因素。
第三,環保壓力大。吳江處在太湖沿岸,環境容量有限,如果存在污水處理不集中、低端產能偷排等情況,會是*大的隱患,絕不能再以犧牲環境來發展經濟。
第四,土地資源供應不足。目前,吳江的工業用地已經超過15萬畝,現在工業用地開發強度達到29%,即將逼近30%的警戒線。
第五,能源消耗總量大。吳江把織造行業列為前期14個“兩高一低”(高能耗、高污染、低產出)行業之一,以盛澤為例,僅一鎮用電量就接近吳江全區總量的一半,主要就是因為紡織行業能耗高。各項要素要綜合評價,而非簡單的加減法所能解決。
如此來看,“升級”已迫在眉睫。
“療舊傷,治未病”
如果你關注吳江地區的新聞,那并不難發現吳江區政府大手筆治污決心。
吳江政府從產業升級的角度考慮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對低端噴水織機的專項治理在紡織行業中引起的反響*大。據悉,吳江力爭用三年時間,將噴水織機總量減少30%,中水處理率從10%提升至****,確保三年之后,噴水織機行業不能有一滴污水排放到水體中。
“其實,對吳江經濟轉型升級來看,**要解決的是發展提升問題,整治是為了提升、關停也是為了提升!”是的,如沈斌所說,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為了整個產業更健康發展在做準備。
過去,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讓不少企業的發展沒了規矩,部分企業甚至無證無照,沒有污水集中處理能力又缺乏監管,如今的整治,其實是在“還舊賬、療舊傷”,陣痛總是要有的。
在沈斌看來,織造行業的提升,不能再繼續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要把好前道,不能到了無證無照的時候再去整治。對于政府經濟發展部門和環保部門,要做到“關口前移”,要加強織造企業的審核,例如上多大規模、是否符合規劃等等都要嚴格把關,例如超出規劃區域,讓周邊百姓怨聲載道的就要調整搬遷,甚至關停,不能再有小農經濟思想,分散發展。
確實,在過去的發展中,我們習慣了末端處理,也習慣了孤立的看待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可這次提升將是一個整體行為。“因為心臟不行問題可能出現在關節、血液”像沈斌打的這個比方一樣,織造行業的整治將整漿并等工序涵蓋其中十分必要。“上漿的漿料是否環保?是否可降解?”吳江近來已經連續關閉了近50家不達標的漿料企業,但仍有部分不符合標準的漿料企業有待整治。
總之,從環保的角度來看,紡織產業真正需要的是“生態化纖、生態織造、生態印染”,可持續的概念要貫穿到每個環節當中。
點擊查看源網頁
延長紡織產業鏈服裝面料“上檔次”
再從能耗的角度來看,進行碳足跡認證也很有必要,要做到生產過程中碳排放的可跟蹤、可計算、可還原、可循環,“我們需要研究企業到底能耗有多少,如果有污染是否采取了清潔化的措施?是否制定了高中低不同層次的清潔生產方案?”
問題已經擺在面前,方法也不是沒有,要解決織造低端產業的提升問題,無非是要解決好能耗高、排污大的問題,吳江政府已經發力,以有形手輔市場“無形手”。
“藥要準,不要猛”
自然,政府的干預也不是肆意而為。沈斌強調,政府管理不能只是號召、搞運動式的行為,而需要先研究技術性的問題,再研究產業發展。
以織造行業為例,除了裝備的革命,還要研究紡織原料方面的問題。比如盛虹集團開發了生物質纖維,進行纖維的循環利用。對吳江地區而言,還需要考慮如何從傳統的里料向面料、家紡、產業用等方面發展,這樣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對噴水織機的使用,產品定位提高了,設備的需求自然也就不同了。
沈斌再次強調,現在所有的改變*終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提升,但要講究提升的方法。
自2013年開始,吳江在推進資源要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做了一些探索。2016年9月,蘇州市全面推廣吳江區工業企業資源集約利用信息系統建設,對工業企業畝均產出、單位排污量產出、單位能耗產出和企業綜合素質進行綜合評價,并積*地向省級相關部門爭取資源要素差別化政策試點,通過差別化土地使用稅、差別化排污權收費、差別化用電政策來倒逼高能耗、高污染行業和企業轉型發展。
在另一方面,吳江區也在大力推進“騰籠換鳳”機器換人,積*推廣自動化水平高的設備工藝、管理和信息技術高度融合來解放勞動力,提高生產效率,以此實現從生產、織造、供應、管理等全流程的改造升級。
談到設備,沈斌認為現在強調工匠精神依然很有必要,現在有些設備我們可能做得出“形”,卻做不出“魂”,他曾見到日本企業技術人員到恒力、盛虹等大企業用戶,任何有效反饋都及時跟進,研發隊伍也十分發達,就像一棵“大樹”,而我們國內的部分企業與之相比則更像“盆栽”,生命力不夠強大。此外,國內依然存在對產業工人不尊重、藍領工人報酬過低、不注重人員培養等多種亟待解決的問題。以上種種,確實值得我們裝備行業企業深思。
對設備的期許、對企業的規范、對未達標者的整治,其中不乏逆耳忠言、苦口良藥,但歸根到底還是那句話,所有舉措的目標只有一個,即產業提升。(紡織機械)
多個“**”卻暗藏危機
正如沈斌所說,沒人可以否定吳江在中國紡織行業發展中的地位。
520萬噸的化纖紡絲生產能力,約占全國產能十分之一,更有恒力集團躋身全球500強;34萬臺織機,年*低產布200億米,可供全國人均15米;如此數量級已經完全顛覆了以往傳統手工業經濟的模式,吳江紡織行業基礎已在。這點從另一方面也能證明——東方絲綢市場,152 0173 3840年10月開始運營,這30年,更直接見證了吳江紡織行業的輝煌:連續多年紡織產量全國**、東方絲綢市場交易額**。
批發市場
中國東方絲綢市場
“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這些‘**’背后也隱藏著危機。”沈斌話鋒一轉說道,這些**都是由原來的粗放經營得來的,整體來看:大而不強、多而不精。“體量是很大,但有些‘虛胖’,數量也不少,但‘專、精、特、新’的不多,導致當前問題越來越凸出。”
沈斌提到,從產業角度來審視,改革開放以來,紡織行業一直在以“攤大餅”的形式粗放發展,可如今,這種模式已經行不通,“面還是那些面,大餅做不了了,那這些面是做餛飩還是餃子?”深入淺出的一問,正是吳江紡織轉型的關鍵所在。
從大的經濟局面來看,以往,緊缺經濟時大部分商品都很暢銷,賣方市場特征明顯,傳統低端產品也不愁銷路,可現在產業進入“天花板”時期,邁入買方市場,消費者對產品質量等各方面需求都提高了,需求差異化也日趨明顯。再看紡織行業,必須承認的是部分紡織企業仍存在“小、散、亂”的情況,前些年有些人用手里的閑錢,買幾臺機器,不講究技術,用做傳統農業的辦法來做工業,也賺到了一些錢,但現在的市場經濟下,這些企業依舊賺錢是不正常的,不賺錢才是正常的。沈斌認為,沒有技術、沒有管理、沒有營銷的模式本就是不符合市場規律的,也自然該被市場淘汰。
曾經在江蘇陽光集團參觀時,有人笑談道,“吳江一車布不抵陽光集團的一匹布”,沈斌承認這是有道理的,因為一方是精益管理,一方則是粗放經營。吳江紡織大量生產基礎布料,卻缺少對面料的深加工。不少行業內人士都曾聽說過“紹興的面料,吳江的里料”“吳江是紹興的白坯市場”,里料自然不如面料值錢,這也難怪有人感慨,“吳江犧牲了環保,卻沒有賺到錢!”以上種種既是產業事實,也是值得反思的地方。
換一種角度,從產業鏈來說,吳江有200億米坯布,卻只有50億米印染,這份不協調是多么明顯的發展瓶頸!再看后道,在吳江幾乎沒有服裝時尚可言,甚至中等或者是特色人群定位的服裝品牌也沒有。
服裝時尚是產業鏈重要的一環
所有癥結都指向了“升級”。
再次細診紡織脈
其實,沈斌對于吳江紡織產業的判斷并非僅僅源于經濟大勢,更有深層原因。
縱觀該地區紡織產業,不難發現有以下幾個明顯特征:**,總體層次偏低,特別是織造環節處在產業鏈價值底端,產品附加值不高;第二,從“十二五”開始,紡織產業整體投資明顯放緩,原來投在化纖、織造的產能已經基本飽和,很難再尋找到新增產能空間,邁入改進需求高峰;第三,效益偏低,從2016年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吳江區畝均稅收可達12.14萬元,而紡織行業只有6.94萬元,低于全區平均水平。其中,化纖14.90萬元、印染13.30萬元、織造4.22萬元,織造行業連畝均稅收值一半都不到。究其原因,大概有兩個:一是終端開票消費較少;二是織造畝均稅收確實偏低。
再從要素層面深入分析,吳江織造產業確實面臨著嚴峻困境:
**,織造產業中部分企業資金供求矛盾凸顯,話語權不足,購買原材料必須現款結算,而產品賣出時又有應收款,甚至部分企業還因擔保造成資金風險,被銀行限貸,此外,還存在庫存導致的產品價格不穩定因素。
第二,勞動力資源緊缺。據調查,目前紡織行業中車間操作工人80%~90%都是外地人,本地人一般更傾向于管理崗位。加之現在的勞動力主力為90后,甚至00后,他們的思想訴求與老一輩不同,選擇工作更注重企業文化、職業發展前景和自我價值的實現,他們寧愿在辦公室少掙一點也不愿意下車間。這也是企業招不到人需要考慮的因素。
第三,環保壓力大。吳江處在太湖沿岸,環境容量有限,如果存在污水處理不集中、低端產能偷排等情況,會是*大的隱患,絕不能再以犧牲環境來發展經濟。
第四,土地資源供應不足。目前,吳江的工業用地已經超過15萬畝,現在工業用地開發強度達到29%,即將逼近30%的警戒線。
第五,能源消耗總量大。吳江把織造行業列為前期14個“兩高一低”(高能耗、高污染、低產出)行業之一,以盛澤為例,僅一鎮用電量就接近吳江全區總量的一半,主要就是因為紡織行業能耗高。各項要素要綜合評價,而非簡單的加減法所能解決。
如此來看,“升級”已迫在眉睫。
“療舊傷,治未病”
如果你關注吳江地區的新聞,那并不難發現吳江區政府大手筆治污決心。
吳江政府從產業升級的角度考慮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對低端噴水織機的專項治理在紡織行業中引起的反響*大。據悉,吳江力爭用三年時間,將噴水織機總量減少30%,中水處理率從10%提升至****,確保三年之后,噴水織機行業不能有一滴污水排放到水體中。
“其實,對吳江經濟轉型升級來看,**要解決的是發展提升問題,整治是為了提升、關停也是為了提升!”是的,如沈斌所說,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為了整個產業更健康發展在做準備。
過去,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讓不少企業的發展沒了規矩,部分企業甚至無證無照,沒有污水集中處理能力又缺乏監管,如今的整治,其實是在“還舊賬、療舊傷”,陣痛總是要有的。
在沈斌看來,織造行業的提升,不能再繼續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要把好前道,不能到了無證無照的時候再去整治。對于政府經濟發展部門和環保部門,要做到“關口前移”,要加強織造企業的審核,例如上多大規模、是否符合規劃等等都要嚴格把關,例如超出規劃區域,讓周邊百姓怨聲載道的就要調整搬遷,甚至關停,不能再有小農經濟思想,分散發展。
確實,在過去的發展中,我們習慣了末端處理,也習慣了孤立的看待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可這次提升將是一個整體行為。“因為心臟不行問題可能出現在關節、血液”像沈斌打的這個比方一樣,織造行業的整治將整漿并等工序涵蓋其中十分必要。“上漿的漿料是否環保?是否可降解?”吳江近來已經連續關閉了近50家不達標的漿料企業,但仍有部分不符合標準的漿料企業有待整治。
總之,從環保的角度來看,紡織產業真正需要的是“生態化纖、生態織造、生態印染”,可持續的概念要貫穿到每個環節當中。
點擊查看源網頁
延長紡織產業鏈服裝面料“上檔次”
再從能耗的角度來看,進行碳足跡認證也很有必要,要做到生產過程中碳排放的可跟蹤、可計算、可還原、可循環,“我們需要研究企業到底能耗有多少,如果有污染是否采取了清潔化的措施?是否制定了高中低不同層次的清潔生產方案?”
問題已經擺在面前,方法也不是沒有,要解決織造低端產業的提升問題,無非是要解決好能耗高、排污大的問題,吳江政府已經發力,以有形手輔市場“無形手”。
“藥要準,不要猛”
自然,政府的干預也不是肆意而為。沈斌強調,政府管理不能只是號召、搞運動式的行為,而需要先研究技術性的問題,再研究產業發展。
以織造行業為例,除了裝備的革命,還要研究紡織原料方面的問題。比如盛虹集團開發了生物質纖維,進行纖維的循環利用。對吳江地區而言,還需要考慮如何從傳統的里料向面料、家紡、產業用等方面發展,這樣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對噴水織機的使用,產品定位提高了,設備的需求自然也就不同了。
沈斌再次強調,現在所有的改變*終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提升,但要講究提升的方法。
自2013年開始,吳江在推進資源要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做了一些探索。2016年9月,蘇州市全面推廣吳江區工業企業資源集約利用信息系統建設,對工業企業畝均產出、單位排污量產出、單位能耗產出和企業綜合素質進行綜合評價,并積*地向省級相關部門爭取資源要素差別化政策試點,通過差別化土地使用稅、差別化排污權收費、差別化用電政策來倒逼高能耗、高污染行業和企業轉型發展。
在另一方面,吳江區也在大力推進“騰籠換鳳”機器換人,積*推廣自動化水平高的設備工藝、管理和信息技術高度融合來解放勞動力,提高生產效率,以此實現從生產、織造、供應、管理等全流程的改造升級。
談到設備,沈斌認為現在強調工匠精神依然很有必要,現在有些設備我們可能做得出“形”,卻做不出“魂”,他曾見到日本企業技術人員到恒力、盛虹等大企業用戶,任何有效反饋都及時跟進,研發隊伍也十分發達,就像一棵“大樹”,而我們國內的部分企業與之相比則更像“盆栽”,生命力不夠強大。此外,國內依然存在對產業工人不尊重、藍領工人報酬過低、不注重人員培養等多種亟待解決的問題。以上種種,確實值得我們裝備行業企業深思。
對設備的期許、對企業的規范、對未達標者的整治,其中不乏逆耳忠言、苦口良藥,但歸根到底還是那句話,所有舉措的目標只有一個,即產業提升。(紡織機械)
百檢網專注于為第三方檢測機構以及中小微企業搭建互聯網+檢測電商服務平臺,是一個創新模式的檢驗檢測服務網站。百檢網致力于為企業提供便捷、高效的檢測服務,簡化檢測流程,提升檢測服務效率,利用互聯網+檢測電商,為客戶提供多樣化選擇,從根本上降低檢測成本提升時間效率,打破行業壁壘,打造出行業創新的檢測平臺。
百檢能給您帶來哪些改變?
1、檢測行業全覆蓋,滿足不同的檢測;
2、實驗室全覆蓋,就近分配本地化檢測;
3、工程師一對一服務,讓檢測更精準;
4、免費初檢,初檢不收取檢測費用;
5、自助下單 快遞免費上門取樣;
6、周期短,費用低,服務周到;
7、擁有CMA、CNAS、CAL等權威資質;
8、檢測報告權威有效、中國通用;
客戶案例展示
相關商品
相關資訊

暫無相關資訊
行業熱點
版權與免責聲明
①本網注名來源于“互聯網”的所有作品,版權歸原作者或者來源機構所有,如果有涉及作品內容、版權等問題,請在作品發表之日起一個月內與本網聯系,聯系郵箱service@baijiantest.com,否則視為默認百檢網有權進行轉載。
②本網注名來源于“百檢網”的所有作品,版權歸百檢網所有,未經本網授權不得轉載、摘編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想要轉載本網作品,請聯系:service@baijiantest.com。已獲本網授權的作品,應在授權范圍內使用,并注明"來源:百檢網"。違者本網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③本網所載作品僅代表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百檢立場,用戶需作出獨立判斷,如有異議或投訴,請聯系service@baijiantest.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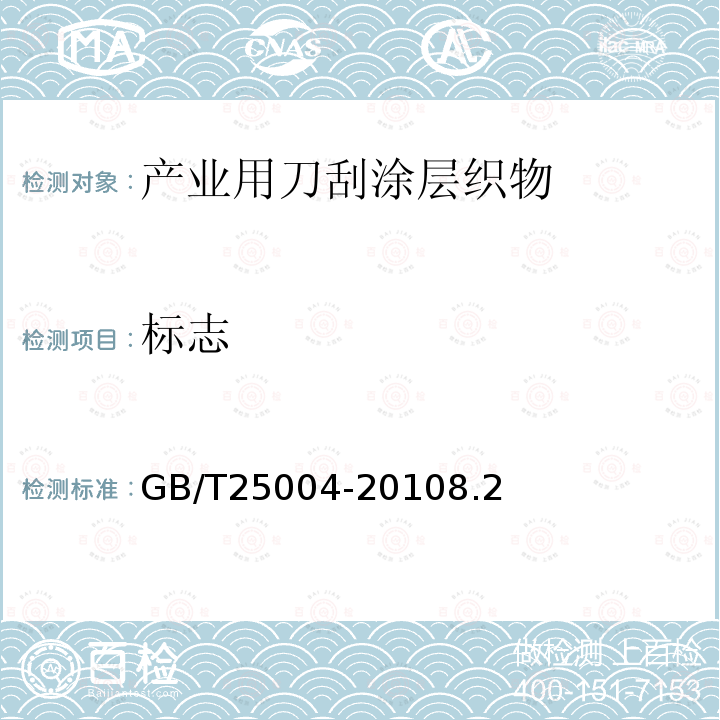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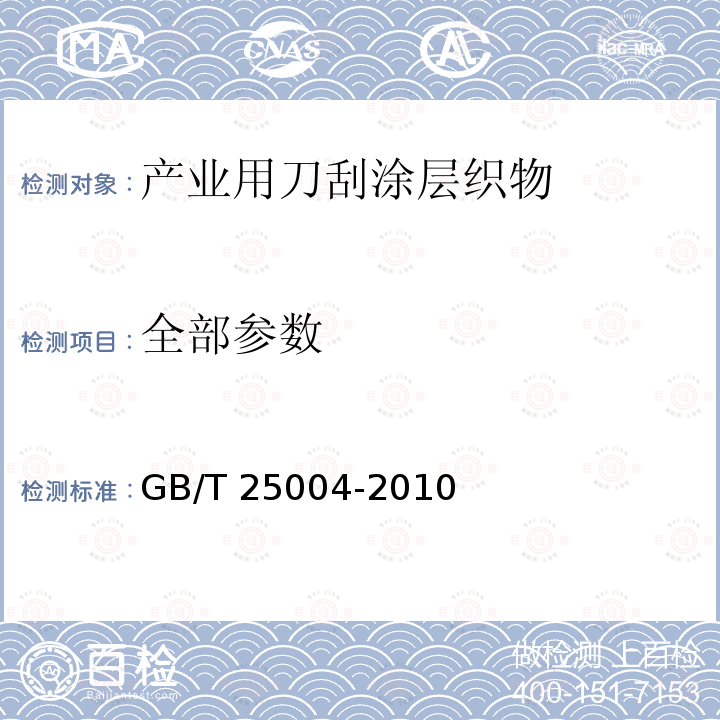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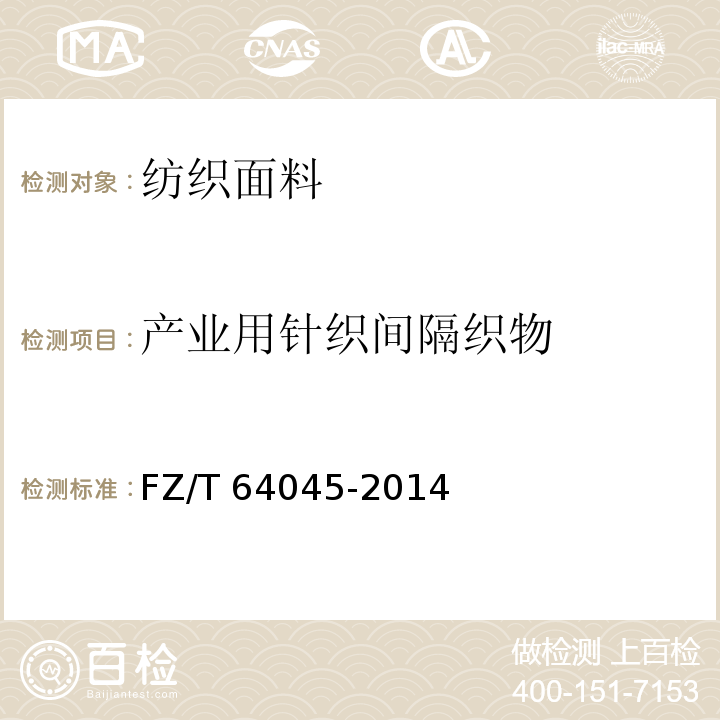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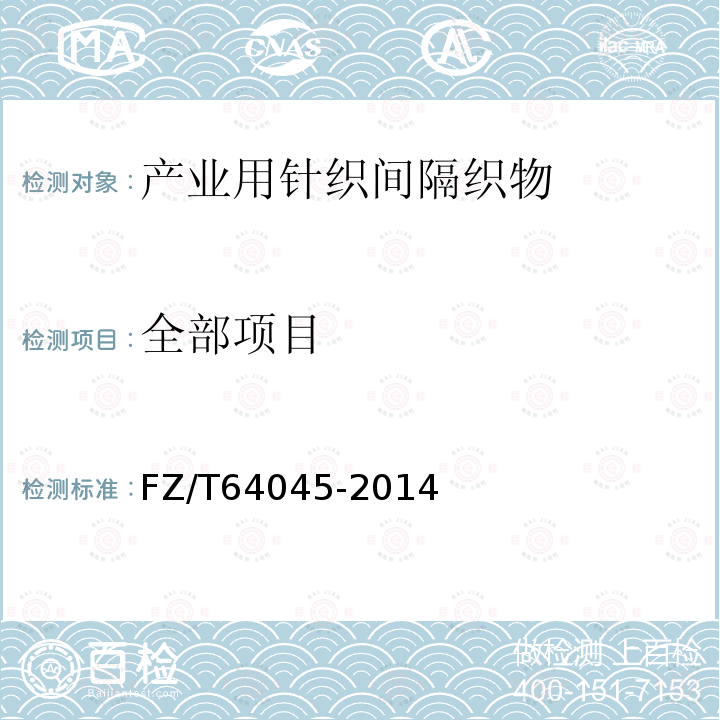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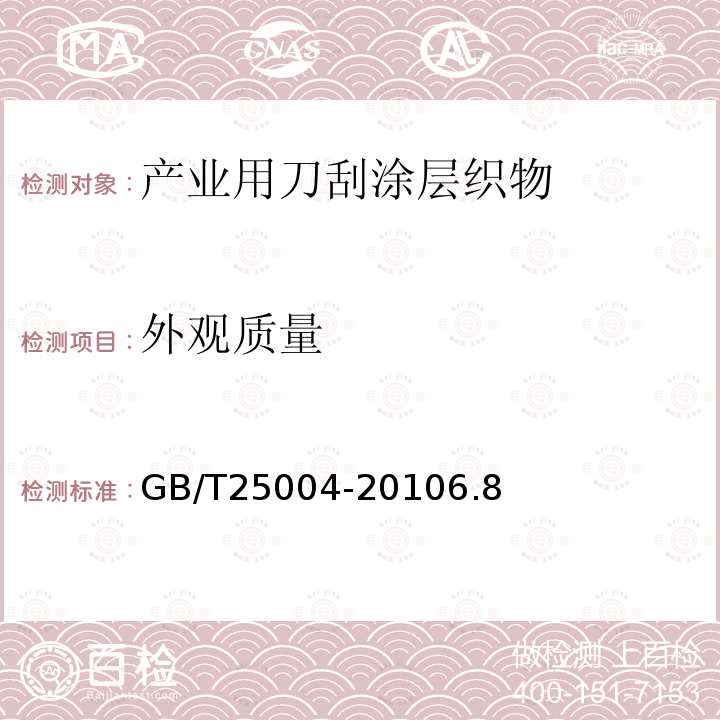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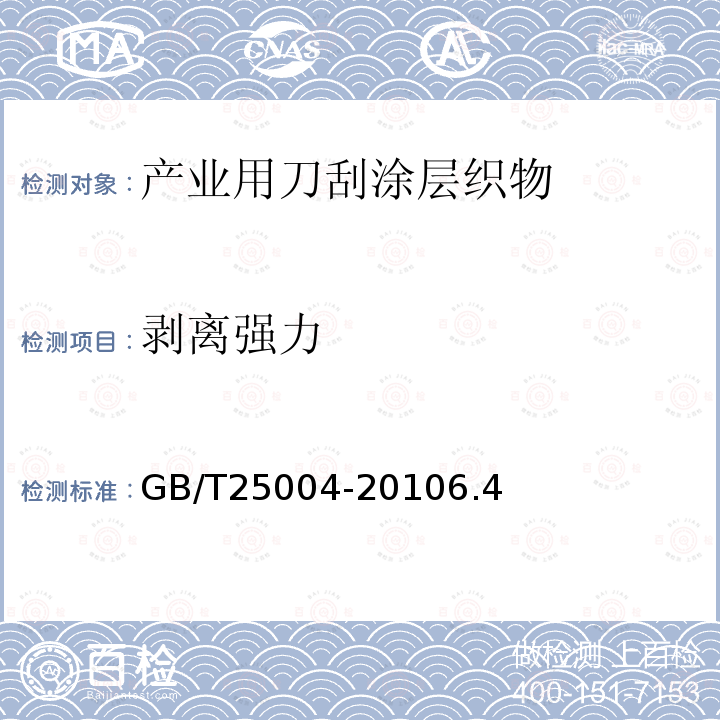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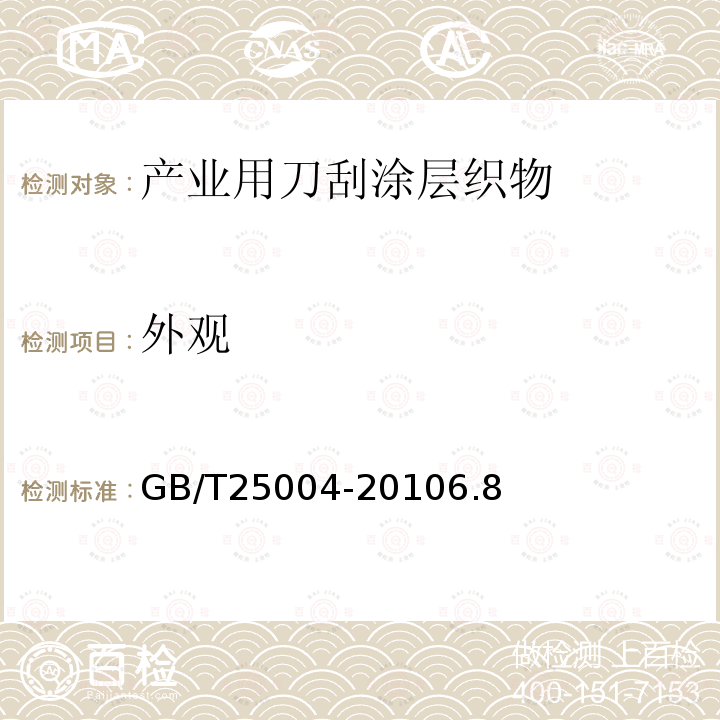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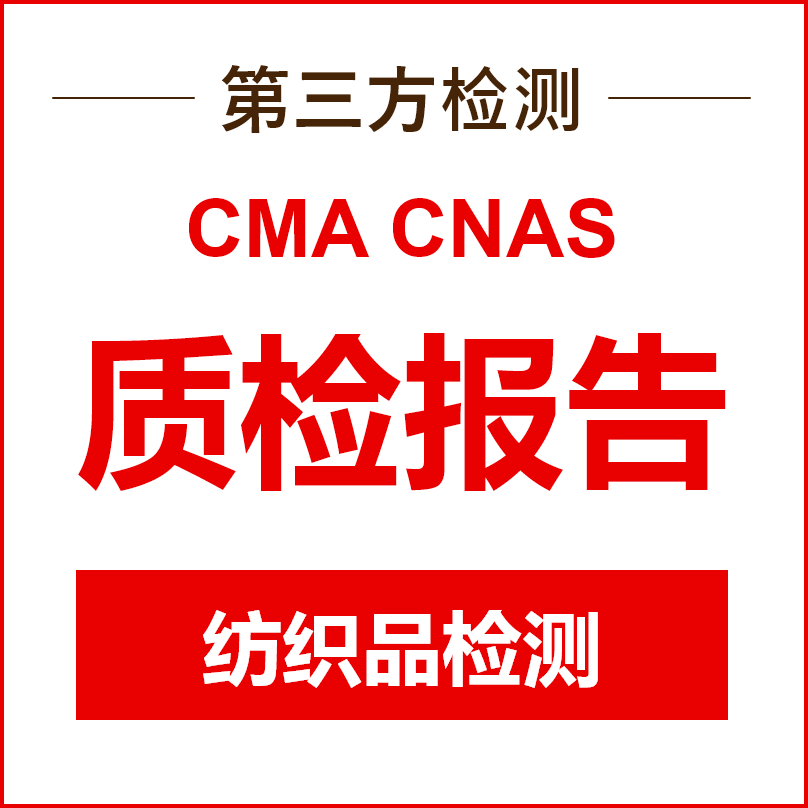







 400-101-7153
400-101-7153 15201733840
152017338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