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情與猙獰:棉花的兩面神形象與帝國之殤
作者:百檢網 時間:2021-12-23 來源:互聯網
我們的世界為什么是我們熟悉的這個樣子? 我們為什么生活在“地球村”? 為什么這個“地球村”有著明顯的等級體系? 為什么大多數人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工廠、公司、機構,然后用所得薪金去購買別人的勞動成果? 為什么我們都生活在一個無形的資本圈中? 我們的生活為什么不呈現另外一種狀態? 幾百年前的世界是這樣的嗎? 是什么讓現在的我們和幾百年前的人類如此不同? 這一切是怎么來的?
沃勒斯坦說,這是“現代世界體系”造成的; 霍布斯鮑姆解釋到,這是“資本的年代”; 彭慕蘭認為,那是因為歐洲人碰巧發現了美洲。他們說得都對,如果沒有全球史的角度,我們對現代世界之所以成為“現代世界”也只能止步于此。只是,切入點在哪里? 撬動世界的軸在哪里? 影響世界的漣漪究竟是由哪塊掉落水中的石頭造成的?
1
哈佛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斯文貝克特( Sven Beckert) 2014年獲得“班克羅夫特”及“菲利普塔夫特”大獎的全球史新作《棉花帝國全球史》(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給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棉花。這個答案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棉花在歐洲工業資本主義興起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已經眾所周知,但從頭梳理棉花和全球資本主義網絡之間的關系還是**次。
造物主賜予人類穿衣保暖的天然資源中,棉花勝過了所有的物種。蠶絲太嬌貴,羊毛太厚重,亞麻纖維短、難染色。棉花溫暖、輕柔、纖維綿長、柔韌性好、易于染色、性價比高,適合全世界不同緯度地區的各種不同人群的著裝要求。在現代世界里,它與我們日日肌膚相親。難以想象,正是這個溫柔的枕畔人創造了一個龐大的“棉花帝國”。“帝國”( empire) 一詞既有文治的顯赫,更暗含武功的偉略,甚至侵略、殖民和霸權。貝克特借此描繪了棉花令人驚悚的兩面神形象: 一面柔情似水,另一面張牙舞爪、面目猙獰。
“帝國”的面相雖然難看,但在貝氏看來,它建立了我們熟悉的現代世界。有關棉花的史學研究汗牛充棟,把棉花放在全球史中來敘述,也并非貝克特一家之言。但貝氏有其獨到之處。他選擇了棉花這個絕好的切入點,以全球的視野,把現代世界的起源和發展圍繞一種商品精煉地敘述出來。雖說用棉花這單一因素來解釋現代世界的形成未免過于簡化,但毋庸置疑,它比其他任何產品都扮演了更加核心的角色。
比如,生產糖的核心技術幾乎沒有什么大的變化,茶、香料等商品的生產也沒有頻繁的技術革新。羊毛、亞麻原材料有限,消費市場也有限。而鋼鐵等重工業本來就是為了滿足棉花的加工銷售才興起的,資金投入多,不靈活。相比之下,棉紡織業所需資金相對較少,技術革新較為容易,一個熟練技術工人就可能改良生產設備,機器購置也相對簡便,而幾乎無窮無盡的市場需求更是推動棉紡織業發展的不竭動力。正因為貝克特洞悉棉花的諸多優勢,才從紛亂的現代世界起源中理出頭緒,給讀者描繪了棉花搭建的剛性帝國。
《棉花帝國》一書共有14章,大致上梳理了以下幾個部分: 第1章追溯歐洲人到來之前的世界棉紡織生產狀況,特別是亞洲地區; 第2至5章討論戰爭資本主義時期和奴隸制的棉花經濟; 第6至8章講述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的起飛階段; 在第9至11章中,作者話鋒一轉,探討美國內戰后世界棉花原料產地的變更; 第12章深度挖掘了擴展到全世界的棉花帝國主義; 在*后的第13、14兩章里,作者將目光放回亞洲,棉紡織業在亞洲重新崛起代表了棉花帝國改變世界的尾聲。
全書追溯了棉紡織業幾個世紀的輪回,如何從以亞洲為主的手工業轉向以英國和歐洲為主的大機器制造業,*后又回到亞洲的過程。這個過程伴隨著全球貿易網絡的重組: 原棉產地、棉紡織生產國、運輸網絡和消費市場全部經歷了重新洗牌。之后,一個等級制的、沾滿壓迫和鮮血的現代世界逐漸浮出水面。
貝氏此著*成功之處,在于“全球”二字。作為哈佛大學“韋瑟赫德全球史倡議”( The?Weatherhead Initiative on Global History) 中心的現任主任,貝氏擁有一個*前沿的全球史研究平臺。這個平臺不僅善于跨越國界來思考文化、經濟、生態、人口的交叉聯系,還提出了要研究更深層次的“全球性的網絡”,即包括一切虛擬和非虛擬的物質、文化、信息流通的渠道。這本著作正體現了中心對“全球網絡”的追求。
2
在貝氏筆下,前現代世界是一個多元中心的世界。全球棉花帶分布在南緯32—35度以及北緯37度的世界三大地區: 亞洲、中美洲、東非。這些地區的無霜期為每年200天左右,溫度不低于華氏50度,降雨量在20—25英寸之間。這三大地區各自獨立地發展了棉花種植和棉紡織技術,并在區域范圍內進行商貿流通。印度次大陸上的人們*早發明從棉花纖維中織出棉線。他們一直擁有世界上*高超的技術,歷來為阿拉伯人、歐洲人所艷羨。與印度幾乎同時,住在今天秘魯海岸邊的土著也獨立發展了棉紡技術。過了若干千年,東非土著也自行掌握了這一技術。歐洲和棉花并無緣分,因為棉花很難在寒冷的歐洲大陸上生長,奧斯曼和阿拉伯中間商又控制著印度和歐洲的棉花交易,加上歐洲人又沒有高超的棉紡織技術,在整個前現代的棉花王國里,歐洲人被擯棄在這三大中心之外。
貝氏指出,這三大中心并不能輕易地被改造、連成一體。地理上的遙遠距離阻隔了它們自然地連接成一體。龐大堅實的奧斯曼、阿拉伯中間商和印度本土的商人群體也不那么容易被取代。*核心的一點是: 雖然棉紡織技術從南亞次大陸、東非、中美洲向外不斷擴張、傳播,且棉花貿易逐漸增長,但種植原棉仍然是各地農民自給自足經濟的一部分,完全不能替代糧食作物生產。農民種植棉花,目的是使自己經濟利益*大化,既保證自己的口糧,也能賺點額外的收入養家糊口。至于遙遠的消費市場,他們并不關心,更不會為了遙遠的市場輕易地放棄糧食作物,改種棉花。
圍繞著如何改造、連接三大棉花中心,貝氏提供了*為豐富、細膩的描述。歸納起來可以分為三大方面: 路、技術、原料。
棉花露出猙獰面目的**步,始于海上航路。要發展,先鋪路。歐洲要**全球,要在世界棉花貿易中獨領風騷,沒有海上航路的鋪設,一切無從談起。
152 0173 3840年哥倫布發現美洲,為歐洲人找到了日后世界原棉*重要的產地和紡織品消費地。1497年,瓦斯科達伽馬成功繞過好望角,避開奧斯曼人控制的世界,開拓了到達印度的新航路。奧斯曼對歐洲人的貿易阻礙從此失效。歐洲人進而獲得了控制棉花產地的入場券。
貝克特在談到歐洲發展航路時,專門用了“戰爭資本主義”( war capitalism)這一說法來指稱歐洲槍炮開道的血腥鋪路過程。他的目的在于強調: 全球資本主義興起并非始于18世紀后期的“工業資本主義”時期,早在歐洲人為他們的全球之旅鋪路時,就已經開始了一場槍炮威逼下的“戰爭資本主義”。
在西方,他們從非洲經利物浦販賣黑奴至美洲各地,建殖民地、種植原棉,利物浦曾一度成為世界黑奴貿易的中心。在東方,幾百年來阻礙他們進入印度、中國的奧斯曼人、阿拉伯人徹底敗下陣來。駝著棉花和各種物資的長長的奧斯曼、阿拉伯商隊消失了,武裝到位的歐洲商船取而代之,橫行于亞歐之間。
技術是近些年反對“歐洲中心論”的學者*忌諱提及的方面。在他們看來,歐洲的技術進步不足以把人類帶入現代世界。但貝氏顯然不這么認為,他花費了大量篇幅談到歐洲人決心在已經開辟的全球海路基礎上把紡織生產移到國內,把消費市場向全球延伸。在紡織技術風起云涌的創新大潮中,英國成了整個歐洲“戰爭資本主義”的*大贏家。
1784年,一個叫塞謬爾葛萊格( Samuel Greg)的英國商人在曼徹斯特附近的波琳河畔建造了一個小型棉紡廠。工廠配備了*新發明的水力紡織機,雇用了一批當地的孤兒做工人,原料用的是加勒比的棉花。貝氏“全球史”的視野在援引的這個例子中表現得****。他仔細考察了這個看似本地的實驗,發現它其實和“戰爭資本主義”打下的全球網絡密不可分。
葛萊格所用的棉花原料是由他的親戚——妻子在利物浦的家族從牙買加和巴西等地買來的; 為了從亞洲人手上把生意搶過來,他千方百計改進生產技術,愿意嘗試*新的機器; 而產品的消費市場也頗為“全球”: 一部分迎合歐洲大陸的消費者; 另一部分通過妻子的家族去往非洲西海岸,滿足那里的奴隸貿易; 或者到達多米尼加島,衣被他自己的家族在那里畜養的黑奴。
葛萊格的星星之火,隨著后來人永無止境的技術革新,從蒸汽再到電力紡織機,迅速擴大為燎原之勢。大機器生產急劇降低了紡織品的價格。貝氏詳細地闡述了英國技術革新的過程,在他看來,如此大規模的技術革新,絕不是印度、中國等原技術**之地通過緩慢技術改進可以企及的。1780年,一匹成品細布要賣到116先令, 50年以后,價格降到了28先令。1830年,一磅重40 支的紗在英國只要1 先令2. 5 便士,同等質量的紗在印度卻要3 先令7 便士。印度失去了產品價廉物美的優勢,從一個生產國轉變為原料輸出國和消費國。
在貝氏看來,正是英國的技術革新能力,使它成為棉花帝國的核心。一旦血管暢通,世界的血液都集中到了英國這顆有力的心臟,再泵出去。貝克特筆下的棉花帝國好比一頭怪獸,一個不斷生長壯大的一元有機體,開始侵吞改造周圍原有的一切。
貝氏描繪的一元帝國里,整合原棉產地是一個*為基礎、艱辛、令無數歐洲商人焦慮的過程。他花了整整三章的篇幅討論世界原棉產地的重要性,更不論其他散落在各個章節中的描述。19世紀之后,為了滿足機器們越來越龐大的胃口,歐洲商人到處尋找可靠、穩定的棉花產地。西印度群島和美國南部原本是*理想的原棉經濟帶,但加勒比海地區革命動亂不止,所有的希望集中到了新生的美國南部。這里土地肥沃,奴隸勞工價格低廉,棉花品種好、產量高。為了滿足采摘棉花的人力需求,黑奴貿易翻了幾倍。貝克特使用了大量數據說明,美國內戰前夕,美國南部已經被認為是棉花帝國的命脈。
然而好景不長。美國內戰一來,原棉供應急劇下跌。在貝克特看來,這一重要轉折加劇了歐洲對亞洲和非洲兩大原中心的壓迫和改造。為了保證原棉供應,英國咬咬牙,在印度鋪公路、修鐵路,加強印度的基礎設施建設,把自己的勢力深入到原先無法控制的印度鄉村,將印度次大陸的原棉生產徹底納入懷中; 俄羅斯干脆把中亞地區變成了棉花城,讓原棉源源不斷地進入俄羅斯的工廠。雖然貝克特并未多談東非的情況,但學者薩迪斯桑瑟里( Thaddeus Sunseri)?的研究也印證了貝克特的看法,德國人在這場競爭中也不甘示弱,他們控制了東非的殖民地,把非洲土著從東非的大片森林中驅逐出去,既按照德國人的科學觀保護了森林資源,又獲得了大量勞動力,迫使非洲人進入德國人的棉花地里工作,還能有效地防止當地土著借藏匿于森林發動叛亂。
至此,擁有了航路、技術和原棉的歐洲,終于開啟了現代世界。
貝氏雖未反對現代世界的到來,但對塑造現代世界的過程和手段頗為不齒。他花費大量筆墨揭露了從“戰爭資本主義”階段到整合、改造三大棉花中心的過程中,每一步暴力、血腥的強迫手段。他并沒有專辟一章節講述壓迫,相反,他的敘述浸透在字里行間。可以說,貝氏不是在敘述棉花帝國,而是在敘述帝國之殤。黑奴貿易的血腥、暴力,奴隸們跨越大西洋的生死掙扎早已為世人所知。而更多的傷痛,因為貝氏的筆墨,被聚集到棉花帝國周圍,足以刺痛讀者的眼睛。
印度次大陸,這個原本富庶的地區,在貝氏看來,是遭受棉花帝國重創的地方。當“戰爭資本主義”去掉了奧斯曼、阿拉伯中間商,印度本土的大量棉花中間商仍在。對于歐洲人而言,這些眼中釘,得去之而后快。印度的棉紡織技術一直****于世界,棉紡織品在世界各地廣受歡迎。其織工掌握著*好的技術,可以把成品自由賣給價高的收購者。這樣一來,歐洲人無法降低棉制品的價格,貿易中的利潤減少。歐洲人通過殖民政府和公司的強力,甚至肉體刑罰,用強加合同的方式,去掉印度中間商,把印度織工變成掙工資者,使他們失去自由定價的能力,以此大幅度提升利潤空間。17 世紀末,一個印度織工可以拿到一匹布價格的三分之一, 100 年后,他們只能拿到6%。而與此同時,歐洲人從印度出口的棉織物大約增長了3 倍之多。
不僅如此,貝克特在敘述歐洲重塑世界原棉產地時指出,控制原棉產地之爭,意味著原先的幾大區域已經不能再保有自己獨立、成熟、運作了成百上千年的經濟圈。印度的例子*為明顯。它從一個既能種植原棉,又有高超紡織技術和銷售市場的經濟區域退化成了單一的種植區域。經濟結構的退化陷印度經濟于危機。不僅僅在印度,非洲、美洲等各地依靠棉花種植生存的人們從此都受世界棉花價格波動的擺布。價格高,還能勉強保持溫飽,價格低,則赤身裸體,無糊口之資,隨時可能餓斃。
1870 年末,印度有600 萬至1000 萬人死于饑荒。時人嘆息: 如果貝拉爾地區始終保持原有的自給自足經濟,就根本不會有饑荒。到1890 年代,饑荒帶來的死亡數據還在上升,包括貝拉爾地區和巴西東北部地區,死亡人數達到了1900 多萬。
貝克特筆下的棉花帝國之殤不僅屬于亞洲、美洲、非洲,同樣屬于該帝國核心區域的歐洲,甚至英國他再次深刻地觸及了“工業資本主義”騰飛的必要條件: 大機器生產對數以百萬計的棉紡織工人長達數百年的剝削。1833 年,愛倫胡通———單身母親瑪麗胡通**的孩子剛滿10 歲,但她已經在棉紡織廠工作了兩年,是個熟練手了。她母親急需她去工廠工作掙工資。她每天早上5 點半到工廠,晚上8 點才結束**的工作。一旦沒有跟上快速運轉的機器,接上紗線的斷頭,她就要被鞭打。愛倫平均一周被工廠監管鞭打兩次,直到她的頭傷痕累累,甚至被罰在脖子上掛上鐵制重物,一遍一遍地爬樓梯。
一百年后,夏衍偷偷溜進上海的紗廠,根據收集到的信息,寫出了**的紀實通訊《包身工》。上海的這些包身工相當于契約奴隸,除了沒日沒夜地工作以外,還受到包工頭、拿摩溫等人的輪番剝削,甚至強暴。直到今天,機器對世界棉紡織工人的奴役之聲仍然不絕于耳。只是,很少有人再關心他們的慘境,甚至有人感謝資本的剝削,還宣稱: 如果沒有機器和工廠,這些窮困的人會更加悲慘。
3
貝克特以棉花為中心的現代世界的起源敘述得頗為成功,并且也****地展現了這個起源的血腥和暴力,這和他長期從事資本、資產階級、勞工、奴隸制的研究有密切關系。從這一點來看,他不愧是個成功的經濟史、資本史的全球史史學家。
一方面,他筆下的棉花搭建的全球化帝國培養了全球化的思維,使人腦洞大開。商人們站在倫敦期貨交易市場,腦子里卻在盤算著巴達維亞、開普敦、澳大利亞、仰光、中國、日本,乃至錫蘭的貿易。人類終于開啟了全新的時代。另一方面,棉花帝國又沾滿了血腥和脅迫。黑奴貿易、小農階層無產化、棉花原產地之爭、殖民地之殤,歷歷在目。甘地醉心于使用家用紡織機,不僅是為了凝聚民族力量,反抗英國殖民者,更是為了抵制張牙舞爪擴張的棉花帝國帶來的經濟方式。
然而,棉花帝國帶給現代世界的絕不僅僅是資本網絡的擴張、經濟方式的改變,還有思想理念的轉換。貝克特相當成功地敘述了棉紡織業從三大中心集中到英國,向俄羅斯、日本等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蔓延,并*終向亞洲回歸的“工業資本主義”擴張的過程,但始終沒能很好地解釋與這個過程相伴隨的一些理念的傳播。其中*重要的就是“民族國家”在全世界的興起。
“民族國家”是現代世界等級秩序的重要基礎,貝氏不僅認可這一點,還多次指出了“民族國家”與“戰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的合謀。在貝氏看來,棉花帝國還從本質上塑造了近代新興民族國家。一些強盛的近代民族國家,如歐洲各國和日本,其棉花商人依靠著民族政權的武力合作,不僅奴役殖民地和棉花經濟帶上的居民,還迫使本國居民從有產者成為無產者,才為棉花帝國貢獻了數以百萬計的勞動力。近代埃及*有活力的時期就是19 世紀中期它的棉花產量連翻5倍之時。
既然如此,那么,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是如何與棉花帝國的擴張聯系起來的??19 世紀末,當中國面臨內憂外患之際,鄭觀應把“商戰”———也就是工業資本主義放置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下來提倡。是什么讓“民族國家”的理念同棉花帝國一起捆綁銷售? 是某種經濟學理論嗎? 還是棉花帝國原本就扎根在“民族國家”的子宮內? 中國的例子完全不是巧合。脫胎于殖民地的新興民族國家政權也沒有改變其與棉花帝國協同合作的本質。
坦桑尼亞獨立后,民族政權在殖民地的基礎上,把人口從原始森林中逼迫出來,試圖進入棉紡織生產。印度民族主義者雖然都承認,19 世紀殖民主義*可怕的影響就是重組了印度的棉花產業,但他們并沒有放棄重組過的經濟結構,相反,還繼續沿著殖民者的設想推動棉花產業,把鄉村的手工藝人變成棉紡織業生產者和消費者。
20 世紀中期的中國也在帝國主義政權撤離后,把棉紡織業的指標作為國力強盛的標桿之一。直至今天,中國夢仍然建立在龐大的棉紡織業基礎上。而人力、綜合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各國也盼望著傳遞棉花帝國的接力棒,發展自己的棉紡織業,以期“強國富民”。為什么在一個向全球迅速擴張的時代,“全球”沒有興起,反而“民族國家”甚囂塵上? 貝氏只談到現象,而沒有闡述這個悖論的源頭。
如果從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角度去思考,快速擴張的棉花帝國沒有給全球提供均質的“想象”,相反,它提供了直觀的差異對比。歐洲內部國與國之間的差異已經大到足夠引起分裂,而亞非拉等地與歐洲之間物質文化的不同,隨著棉花帝國的擴張,變成了鴻溝。這種差異在人們往返的敘述中逐漸固化,引起差異的想象。
現代世界的建立既不能缺少了英國人對自己的自豪,也不能缺少了印度人對自身困境的想象。再者,如果從資本的角度去思考,棉花帝國所創造的巨額資本是不是必須要有一個積累、管理和分配的有效平臺? 這個平臺是不是就是“民族國家”? 如果是這樣,那么貝克特不僅要描寫各個民族國家政權對資本的支持,更應當闡述其和資本之間共贏、共生的局面。可憾的是,貝氏只略微談到了英國政府早期和資本之間的共生狀態,對其他例子幾乎未置一詞。“民族國家”對其他政權產生的吸引力因此不得而知。
另外,貝克特雖*為關注美國內戰對棉花帝國轉型造成的巨大影響,卻很蹊蹺地忽略了20 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對棉花帝國的作用。他用工資來解釋棉花帝國的南移,隨著歐洲和美國北方地區工會組織日漸強大,產業工人工資快速上漲,使得勞動力成本低廉的亞洲等地取代歐美,成為棉紡織中心。這一解釋看起來順理成章,實則過于簡化。
雖然他曾指出,由于歐洲忙于**次世界大戰,亞洲棉紡織生產得以乘隙大展拳腳,加速了棉花帝國向亞洲轉移。但這兩場戰爭究竟給歐洲帶來了什么呢? 工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棉紡織生產徹底讓路? 戰后殖民地的大幅度萎縮是否*終使得歐洲的棉紡織工業無利可圖? 不回答這些問題,只強調勞動力成本,棉花帝國南移之路便成了一個簡化了的、片面的故事。就像貝氏解釋現代世界的起源一樣,棉花帝國只是現代世界形成中的一個關鍵卻片面的版本。
全球史寫作能否成功,還有一個關鍵因素: 是否能夠準確把握各個國家地區的歷史。貝氏著作中有關中國的部分*為簡略,但中國在歐洲興起之前相當長的時間內一直是棉紡織手工業大國。除印度以外,中國的棉紡織業一直處于世界*前列,更不用說近年來中國的棉紡織生產占全球三分之一,遠超世界所有國家。這樣一個大國在棉花帝國中的位置究竟如何,它怎樣從一個家庭手工業轉變成大資本、大機器生產的工業?
這完全不是貝氏幾段話就可以囊括的。貝氏的關注點都放在印度,如果說印度歷來是世界棉花和棉紡織品出口的重地,那么它和中國的原棉種植和棉紡織品生產有什么異同? 貝氏*少談到中國的棉花,是因為19 世紀以前中國的原棉一直自給自足嗎? 當鴉片戰爭迫使中國開放了通商口岸以后,中國龐大的原棉產量對他們意味著什么? 為什么貝氏只關注了19 世紀90 年代以后的中國棉紡織產業? 這中間的半個世紀,中國的原棉種植和棉紡織業對歐洲的棉花帝國有什么影響??
要知道,美國南方———歐洲原棉*重要的供給地,直到美國內戰前夕,其原棉產量也僅僅和中國差不多而已。是中國的原棉難以運輸? 還是質量較差? 還是貝克特根本沒有能力了解中國的情況? 總之,對世界上如此重要的一個棉紡織生產大國語焉不詳,大大削弱了棉花帝國全球史的“全球性”。
貝氏雖然試圖用“全球”的視野來擺脫歐洲中心論,但他在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路徑上仍然持有明顯的偏見。他簡單地認為,全球棉紡織工業的發展遵循了這樣一條道路: 即家庭作坊消失,農民無產階級化,進入大機器生產。所以他在棉花帝國南移的過程中簡單地把這個路徑套用到了各個復興的棉紡織生產國之上。可事實上,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直到二戰以后還保持著家庭棉紡織和大機器生產并作的局面。
以中國為例,農村手工棉紡織業競爭力急劇下降,但不代表著農民就無產階級化。相反,赤貧的農村家庭雖不能再為市場提供棉紡織品,但婦女們繼續為自己家庭所需紡織,因為普通農村家庭仍然購買不起機器生產出來的布匹。19 世紀末20 世紀初,蘇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的工廠,雖然他們的工資收入超過了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收入,但仍然不足以滿足城市的消費,留在蘇南農村的家庭留守勞動力就進行土布生產,供給在城里的家庭成員,以減少他們的生活壓力。
而在上海以北的通海地區,由于洋紗價格和原棉相差無幾,手工紡紗無利可圖,婦女遂放棄家庭紡紗,改從市場購買,或者由家中年幼的女孩進行紡紗,而由年長的、技術成熟的婦女織布,或自用、或出售。張謇大生紗廠出的紗多數都由通海本地織成土布。這種不完全的工業資本主義發展途徑在中國至少持續到了20 世紀中期,離它首次在中國出現已經有半個多世紀之久。因此,棉花帝國南移之路根本不是貝氏描述的那樣快速迅捷,相反,它充滿了貧窮的抵抗。正是這種貧窮的抵抗,使人深思工業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的暴力,也再一次提醒全球史史學家,警惕“全球”視野背后的歐洲中心觀。
(來源:網易;時間:20180709;鏈接:http://news.163.com/18/0708/11/DM6KDD50000187UE.html)
百檢能給您帶來哪些改變?
1、檢測行業全覆蓋,滿足不同的檢測;
2、實驗室全覆蓋,就近分配本地化檢測;
3、工程師一對一服務,讓檢測更精準;
4、免費初檢,初檢不收取檢測費用;
5、自助下單 快遞免費上門取樣;
6、周期短,費用低,服務周到;
7、擁有CMA、CNAS、CAL等權威資質;
8、檢測報告權威有效、中國通用;
客戶案例展示
相關商品
相關資訊

行業熱點
版權與免責聲明
①本網注名來源于“互聯網”的所有作品,版權歸原作者或者來源機構所有,如果有涉及作品內容、版權等問題,請在作品發表之日起一個月內與本網聯系,聯系郵箱service@baijiantest.com,否則視為默認百檢網有權進行轉載。
②本網注名來源于“百檢網”的所有作品,版權歸百檢網所有,未經本網授權不得轉載、摘編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想要轉載本網作品,請聯系:service@baijiantest.com。已獲本網授權的作品,應在授權范圍內使用,并注明"來源:百檢網"。違者本網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③本網所載作品僅代表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百檢立場,用戶需作出獨立判斷,如有異議或投訴,請聯系service@baijiantest.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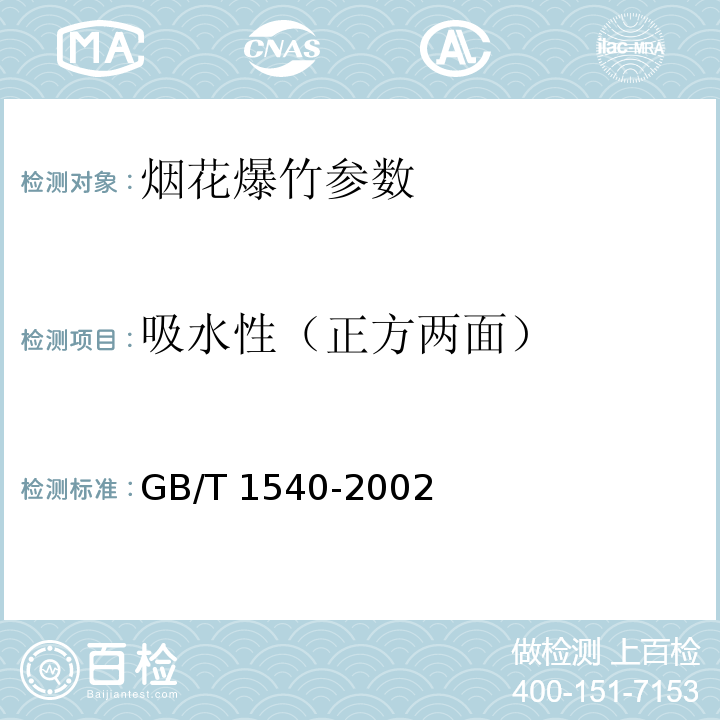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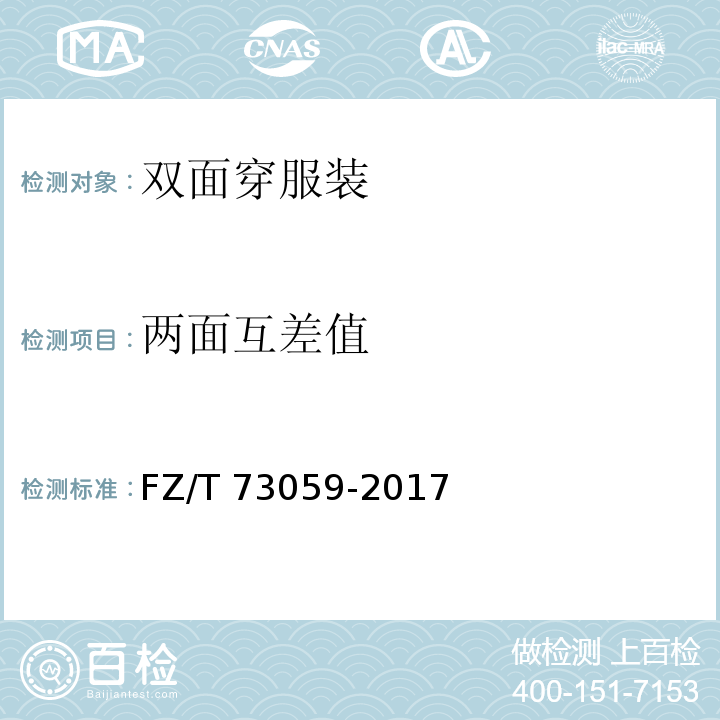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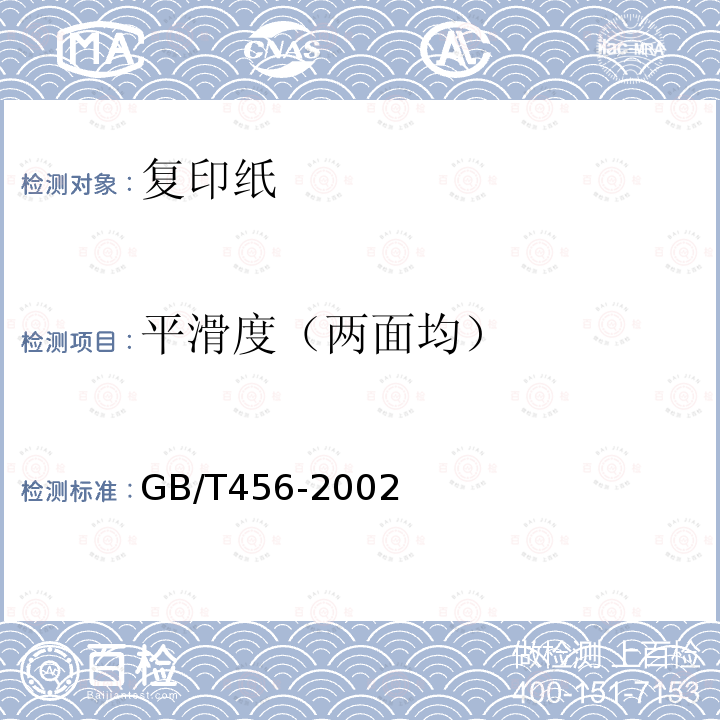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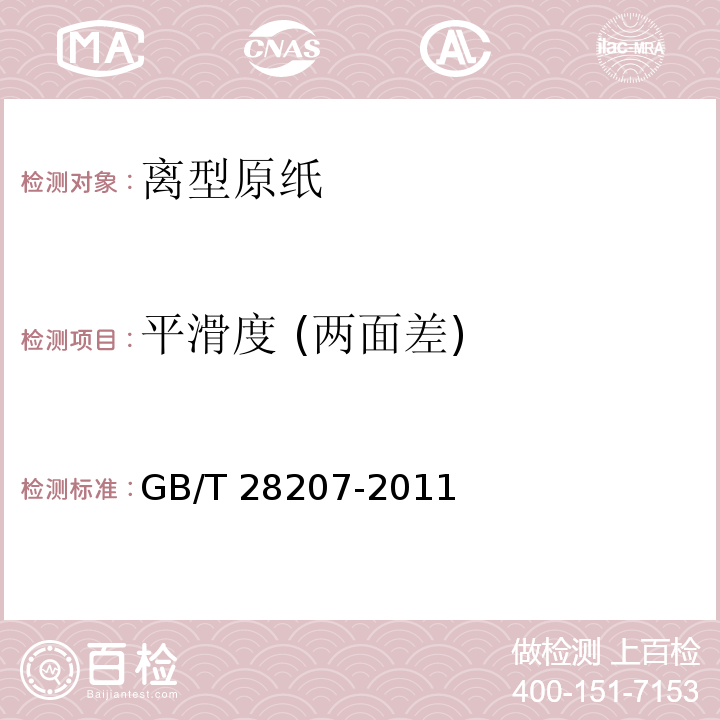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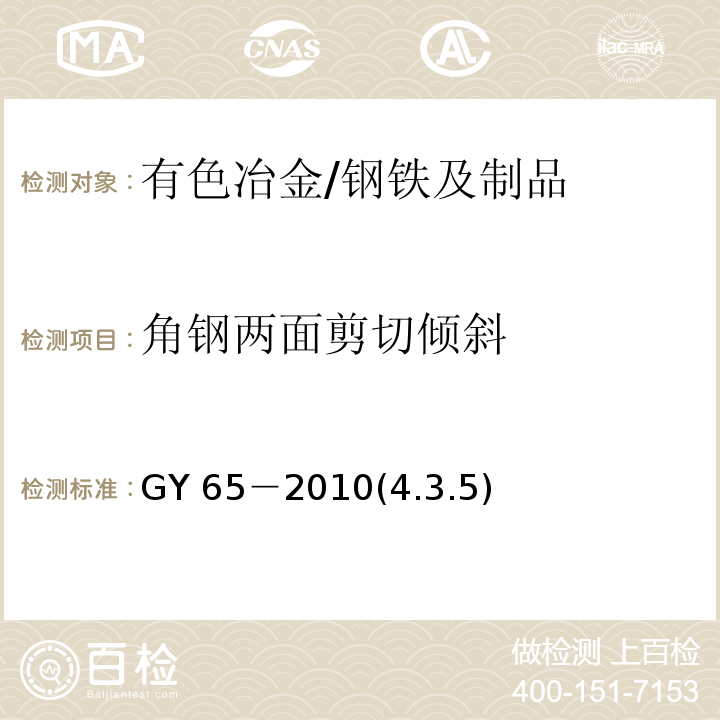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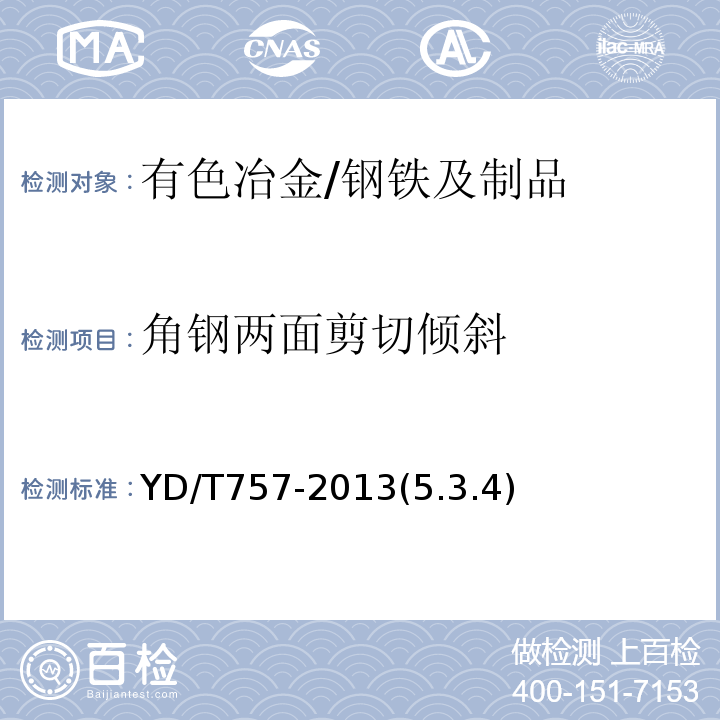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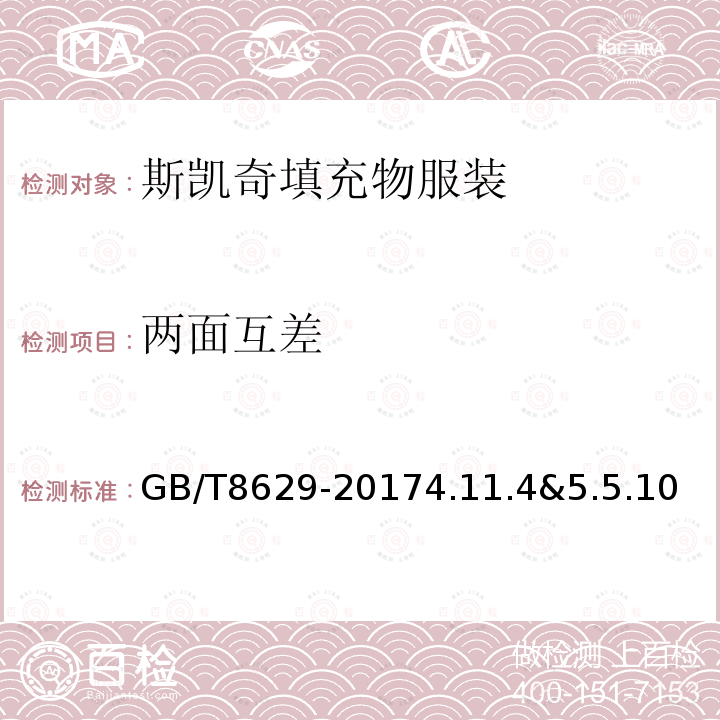











 400-101-7153
400-101-7153 15201733840
152017338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