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的全球史》:解釋一件商品,就是記錄一部全球歷史
作者:百檢網 時間:2021-12-23 來源:互聯網
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身穿的一條牛仔褲,可能源自印度提供的棉花,日本的加工,面上再貼著美國的品牌標簽。在這種現象的背后,是商品生產及貿易的國際性分工,是一幅跨越國界的人類合作的宏大畫卷。歷史學家們發現,以民族國家為研究框架似乎已不能很好地解釋這種現象。仿造陳寅恪先生的名句,可以說,“解釋一件商品,就是作一部全球歷史”,《棉的全球史》這部書為這句話提供了一個注腳。
棉:全球化歷史的透鏡
《棉的全球史》的英文原名是“Cotton: The Fabric That Made TheModernWorld”,直譯為中文應該是“棉:塑造現代世界的織物”,中譯本將其譯為“棉的全球史”,應該說基本符合這本書的內涵。這本書獲得了世界歷史學會2014年杰里本特利獎。作為全球史研究的重要組織,世界歷史學會自152 0173 3840年起設立圖書獎(于2012年起更名為杰里本特利獎),每年評選一到兩部該領域內的佳作。**的彭慕蘭的《大分流》,就是2001年的獲獎圖書。
《棉的全球史》試圖以“棉”為透鏡,來觀察與棉有關的全球現象,梳理棉的全球化過程。簡單地概括,《棉的全球史》主要討論兩個問題:**,全球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從11世紀開始,棉已經實現了“全球化”,這對后來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有著潛在的影響;第二,歐洲(或者說英國)后來居上,取代印度成為了棉的全球化體系的中心。
關于棉紡織業發展的研究并不少,大多集中在19世紀以來的時間段,《棉的全球史》則將目光投向了更加遙遠的過去,去追溯19世紀以前就已經存在的“全球性”體系。《棉的全球史》認為,棉的全球化歷史中存在著前后兩個體系。一個是約1000年至1750年,以印度為中心的舊棉紡織體系。這個體系是“離心”的,印度雖然是核心但并不主導其他地區。印度是棉花栽培的發源地,而且根據考古發現和實物證據,印度的棉紡織品傳播到了東亞、中東等不同地區,形成了一個以印度洋為中心的流動空間。另一個是約1750年至2000年,以歐洲西北部為中心的新棉紡織體系。歐洲通過學習和交流,經歷了幾個世紀的積累,后來居上地成為全球核心,并影響著其他地區的生產和消費。這是一個“向心”的體系,歐洲的棉紡織業從其他地區“剝削”著資源和利潤。
《棉的全球史》重點解釋了為何會發生舊體系向新體系的轉變。探討歐洲或者英國為何成為全球棉紡織業的中心,很容易跟“工業革命為什么發生在英國”“資本主義為什么產生在歐洲”這樣的宏大問題聯系起來。既往的解釋大多有一個共同點:歐洲在影響著世界。而《棉的全球史》認為是世界影響了歐洲。《棉的全球史》嘗試提供新的解釋:在舊的體系里,歐洲的棉紡織業相比印度、中國等其他地區明顯落后,歐洲的崛起是不同因素“疊加”的結果,有一些因素是歐洲自身特有的,有一些是從別處學習而來。
沃勒斯坦和彭慕蘭的影響
為何會選擇棉為對象?又為何將棉的全球化追溯到11世紀?這可以總結為作者受全球史既有研究的影響。該書作者喬吉奧列略曾經長期參與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全球經濟歷史網的工作,比如編輯《紡織的世界》《印度如何衣被天下》《全球設計史》,這些經歷奠定了他選擇棉的研究基礎。在今天,全球紡織品和服裝的出口額已經以千億美元計,亞洲恢復了曾經的棉紡織業優勢,中國成為全世界*大的紡織品出口國。這種現狀可能刺激了對西方中心論的重新審視,也是《棉的全球史》寫作的現實背景。
研究某件全球性的商品,是全球史研究的慣用套路,棉當然是合適的一種。如同首都師范大學全球史研究中心主任劉新成教授所言,全球史研究有一個典型模式,即產生于某個地區的發明創造如何在世界范圍內引起連鎖反應,比如棉花生產。在全球史家的眼里,在歐洲作為一個全球貿易實體出現很久之前,其他地區的商人就已經將東半球大部分地區連結成為一個大范圍的貿易世界,古代中國和地中海之間的絲綢之路、阿拉伯半島和印度之間的海洋航線,很早就已經是充滿活力的交通線和貿易網。
列略坦承自己受到了沃勒斯坦的影響。《棉的全球史》可以看到沃勒斯坦世界經濟體系理論的影子,舊的棉紡織體系具有松散的、非政治意義的特征,印度和歐洲的中心—邊緣關系在新體系里被倒轉,而20世紀以來,這樣的關系又被重新改寫。不過,列略堅信自己對沃勒斯坦有所超越。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被質疑是歐洲中心主義,《棉的全球史》所勾勒的世界體系的上限則往前推進到11世紀;與沃勒斯坦不同,列略認為他筆下的棉紡織體系不僅包括權力和金錢,還包括產品、時尚和技術,換言之,他筆下的體系要比沃勒斯坦的內涵更加豐富。
彭慕蘭的“分流”觀點,列略也有所借鑒。彭慕蘭指出的歐洲與中國的“分流”發生在18世紀晚期,原本與中國擁有相同條件的歐洲,因為一些偶然因素突然拉開了與前者的差距。列略指出這種“分流”現象也發生在18世紀以來歐洲和印度、中國的棉紡織業中。但是,與彭慕蘭筆下似乎偶然發生的“分流”不同,列略認為,集中在一個特定的時間段進行分析,會導致縮水與偏頗的風險,歐洲(或者說英國)成為全球棉紡織業的中心,在以往的敘事中似乎是突然而迅速地發生的,實際上,這可能是經過了幾個世紀的漫長而緩慢的積累才形成。因此,列略筆下的“分流”過程持續了好幾個世紀,而且歐洲是在許多方面落后的情況下追了上來。
全球史研究存在的通病
全球史研究似也存在一些通病。如錢乘旦先生指出,全球史的一個內在缺陷是基本上不用一手資料。這一缺陷難免導致對非母語史料的錯誤解讀和臆測,當年彭慕蘭《大分流》誤認為明代中國需要用3天來織一匹棉布,就遭到了黃宗智的批評。
《棉的全球史》也未能幸免。列略的研究幾乎全依靠英文資料進行,對來自非英語國家的文獻只能使用翻譯文本,其使用的數據大多是來自前人研究的二手資料,難免導致知識上的硬傷。在第322頁,列略稱:直到19世紀末,英國和歐洲的棉紡織品在中國都少有人氣,直到1880年代,中國都只有少量棉紗和布料進口。實際上,英印棉紗因其低廉的價格,排擠了中國本土棉紗,導致了國人用洋紗進行織布,這是不爭的事實。鴉片戰爭前,中國和英國之間的棉紡織品對流中,中國就已經出現了入超,到1867年,棉制品占據當年全國進口總值的21%,僅次于鴉片,這個比例在19世紀后半期一直維持在30%上下;在1879年,從印度輸入中國的棉紗達到了驚人的3000萬磅。這些資料在前輩學者嚴中平先生所著《中國棉紡織史稿》、彭澤益先生所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中都可以看到。
“解釋一件商品,就是記錄一部全球歷史”并不是新鮮現象,比如關于茶葉、糖、絲綢等商品,均有全球史研究,這些研究看似同類又有區別,區別可能在于對既有研究模式的借鑒和突破程度,以及對一手史料的挖掘利用程度。
《棉的全球史》或許能引起我們一些思考,比如如何更好地發揮中國本土史料在全球史研究中的作用,如何用全球史的視角觀察中國的棉紡織業。棉自宋元傳入中國至今,也有豐富的事跡可說,南京土布也曾出口海外。我們期待有中國學者能夠充分利用本土文獻后寫出一部中國“棉”的全球史。(肖峰)
(來源:中華讀書報-光明網;時間:20180323;鏈接: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8-03/07/nw.D110000zhdsb_20180307_2-10.htm?div=-1)
百檢能給您帶來哪些改變?
1、檢測行業全覆蓋,滿足不同的檢測;
2、實驗室全覆蓋,就近分配本地化檢測;
3、工程師一對一服務,讓檢測更精準;
4、免費初檢,初檢不收取檢測費用;
5、自助下單 快遞免費上門取樣;
6、周期短,費用低,服務周到;
7、擁有CMA、CNAS、CAL等權威資質;
8、檢測報告權威有效、中國通用;
客戶案例展示
相關商品

相關資訊

行業熱點
版權與免責聲明
①本網注名來源于“互聯網”的所有作品,版權歸原作者或者來源機構所有,如果有涉及作品內容、版權等問題,請在作品發表之日起一個月內與本網聯系,聯系郵箱service@baijiantest.com,否則視為默認百檢網有權進行轉載。
②本網注名來源于“百檢網”的所有作品,版權歸百檢網所有,未經本網授權不得轉載、摘編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想要轉載本網作品,請聯系:service@baijiantest.com。已獲本網授權的作品,應在授權范圍內使用,并注明"來源:百檢網"。違者本網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③本網所載作品僅代表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百檢立場,用戶需作出獨立判斷,如有異議或投訴,請聯系service@baijiantest.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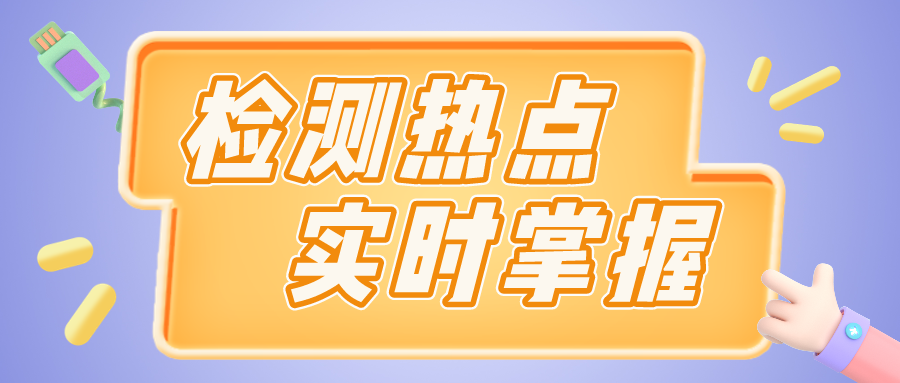






 400-101-7153
400-101-7153 15201733840
152017338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