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賓,教授,材料學博士,美國阿克隆大學博士后,教育部創新團隊“有機/無機雜化功能材料的設計構筑及其纖維成型”成員,上海市優秀技術帶頭人。長期致力于成纖用有機無機雜化功能材料及其改性熱塑性高分子纖維(占化纖總量80%以上)的研究和產業化技術轉移,在成纖用功能納米材料表面設計、合成及其在高分子材料改性和纖維/薄膜成型加工應用方面取得一定研究成果,作為團隊骨干,榮獲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上海市技術發明一等獎等科技獎勵。
從上游的原料開發、聚合物的合成和纖維的加工,中游的紗線制造和印染加工,再到下游的面料開發、服裝生產、品牌營銷,紡織服裝產業鏈的每個細分環節在整個紡織工業中都有著重要的驅動力,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一方經濟、科技和環境的迭代發展與建設。近日,記者來到位于紹興市柯橋區科技園的惠群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就“鈦系催化劑在聚酯產業中的研發應用與推廣”對東華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孫賓進行了專訪。
聚酯生產催化劑“銻換鈦”的必要性
聚酯,是指由多元醇和多元酸縮聚而得的聚合物的總稱。在其生產過程中,催化劑加入到乙二醇中可以合成聚酯原料,再往乙二醇中加入另一種原料就能合成生產所需的樹脂,此時,小分子經聚合后變成了高分子,再通過紡絲加工就能形成短/長纖,*終應用于面料之中。
從催化劑的元素特性來看,銻系催化劑具有一定致癌性。在高溫條件下,銻會發生遷移,從人們日常使用的滌綸衣物、飲料瓶和包裝膜之中遷移出,從而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造成威脅。因此,GBT152 0173 3840規定:每公斤面料中銻的溶出量不能超過30毫克,而未來的產業共識則是逐步取締銻系催化劑,目前,化纖行業協會已主持通過了無銻聚酯樹脂、纖維的系列檢測標準,要求每公斤無銻滌綸面料中銻的含量不能超過10毫克,該系列標準目前已進入報批階段。
事實上,早在2010年,國內的產業界和科研界就已經形成較強的“銻換鈦”的意識,但受制于技術和資金等因素,當時的聚酯生產商并沒有太強的驅動力,近年來,隨著國家相關政策的普及推廣,廠商和行業協會對綠色生態和環境保護日益重視,各方逐漸形成了“銻換鈦”的共識。然而,目前國內聚酯廠商生產的產品和國外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而每年的聚酯產能卻有5000-6000萬噸,許多高品質的鈦系催化劑仍舊掌握在美國杜邦、德國阿考迪斯、日本帝人等公司手中,為避免在關鍵技術和基礎材料上受制于人,孫賓教授表示,希望國內的聚酯材料生產商能跟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鈦系催化劑協同,推進其生產線應用,這樣才能保證日后國內鈦系催化劑的自主供應。誠然,鈦系催化劑具有安全環保、綠色節能、高活性等特性,但由于其在聚合反應中的熱降解速率是銻的2倍左右,會使*終成品看上去偏黃,給產品品質帶來一定影響,并給生產線應用帶來影響,特別是產能超十萬噸的大容量熔體直紡聚酯生產線上的應用更是如此,因此,孫教授認為,“鈦系催化劑的普及應用,仍有較大的技術難題需要攻克,需要產業鏈上下游協同攻關”。
眾所周知,滌綸衣物染色的高溫環境會使銻析出,在印染污水排放時,會給水體帶來一定污染。從產業地域來看,紹興集聚了國內大量的紡織印染廠家,數據顯示,2020年紹興紡織印染產業總產值達到500億,占全國紡織印染產業總產值的近36%,催化劑的銻換鈦對紹興當地的企業來講同樣勢在必行。
企業家和民眾意識的覺醒將推動聚酯產業的技術革新
聚酯合成過程中的酯化反應會產生水,造成催化劑水解,進而影響加入催化劑的活性和效能,所以大部分鈦系催化劑是在酯化結束后的預縮聚階段加入。源自東華大學的雜化鈦催化劑(DH-HyTi catalysis)因其耐水解的特性可在酯化前或酯化階段加入,更好地發揮酯化催化作用,進而提升酯化效率,在降溫節能、生產效率提高和特種聚酯的生產方面**開發價值。故而,鈦系催化劑的高活性所帶來的聚酯生產效率的大幅提高未來也有待進一步開發應用。據此,孫教授認為,“鈦系催化劑的應用在推動聚酯產業鏈綠色化的同時,還會帶來技術的革新”。對于目前國內的聚酯生產商來講,需要解決的技術難點在于如何利用現有的適合于乙二醇銻催化劑基的聚酯生產裝置及工藝、纖維加工工藝,同時保證金屬催化劑的活性和高效,孫教授表示,聚酯裝備設計方可提前進行產業布局,按照鈦系催化劑的技術特點來設計聚酯生產成套裝備,這樣才能充分發揮鈦系催化劑的優點,協同**聚酯行業的綠色低碳發展。綜上,孫教授認為,鈦系催化劑的逐步推廣和應用有四方面的要素不可或缺:**,國際產業界的倒逼;第二,催化劑制造和使用成本降低,即規模效應的形成;第三,產業界企業家意識的覺醒;第四,國家層面的政策推動。
惠群新材料――高新技術產品化、商品化的孵化器 技術轉移的橋梁
問:請孫教授簡要描述一下惠群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定位和發展戰略
孫賓:
早年我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時發現,美國的企業會委托高校的教授做原創性的研究,且企業有專業的工程化技術團隊和中試平臺可以將實驗室的高新技術成果轉化為市場化的產品,經過市場檢驗之后就能投入大規模的生產,產生大量的原創新高新技術產品,這也是美國的技術比較**的原因之一。
從國內來看,雖然每年高校也會有很多技術成果產生,但是由于缺少與之相匹配的工程化技術團隊和中試平臺,對技術*終走向市場會帶來一定限制。因此,惠群新材料的定位是希望通過企業和高校的對接,將其打造成一個高新技術產品化和商品化的孵化器,一個融接實驗室成果和高技術產品/商品的橋梁,實現從“0-1”的突破,進而形成協同創新的產業聯盟,推動紡織產業鏈上下游的發展創新。例如,我今天講到的鈦系催化劑,惠群已經有了一定的技術成果,已經能夠批量生產和供應,目前也在上下游的企業得到了試驗和應用。
自下而上的需求傳導將影響產業的*終變革
問:孫教授認為,鈦系催化劑在紡城企業中的推廣應用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孫賓:
**我認為,中國輕紡城是外貿導向型的紡織集聚區,也是纖維綠色化、功能化的集聚區,每年有大量的紡織品從這里走向世界,在“杭紹甬”一體化戰略的推動下,這里科技成果轉化的氛圍、政府的服務意識、對人才的支持在全國范圍內來講都是比較全面的,這一點我當時在推動惠群新材料這個項目落地時就有所體會。
其次,對于鈦系催化劑在輕紡城企業中的推廣,我認為*重要的一點是下游的面料商要有品牌轉型的意識,也就是技術團隊根據面料企業的需求,結合企業實際情況定制一套個性化的技術升級方案,從而自下而上地給整個產業鏈帶來改變。我們在推廣這項技術時,也渴望有更多品牌商加入,和我們一起共同推進產業變革。拿具體的面料來說,除了銻換鈦帶來的綠色健康外,在纖維原料生產過程中加入有機無機雜化功能材料可賦予纖維抗菌、抗病毒、阻燃、消光等特性,從而提升面料的功能性,增加產品的附加值,那么現在東華大學的紹興創新研究院就提供了新材料功能母粒的研發平臺,可以為有需求的面料企業提供相應的技術支撐。
古希臘數學家、物理學家阿基米德曾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起整個地球”。同樣,“鈦系催化劑,不僅僅是無銻”。她的推廣應用,不僅僅是化學元素的簡單替換,同時也會帶來產品的綠色化、“卡脖子”先端材料的自主化、能源的節省和生產的增效等產業的變革,這背后需要民眾意識的覺醒,政府政策的支持,資本的介入,才能*終實現技術的變革,推動產業經濟的良性和循環發展。
(文/圖 唐宇昕 統籌/孫怡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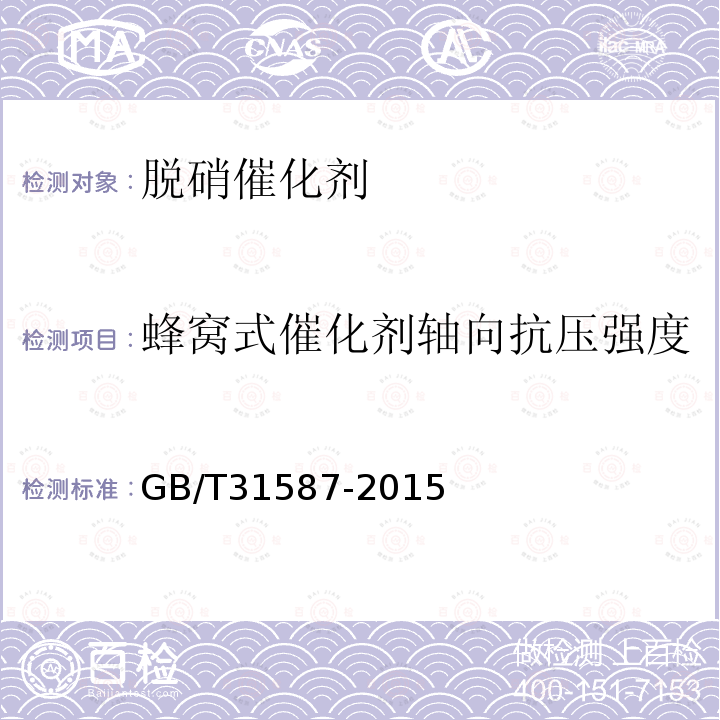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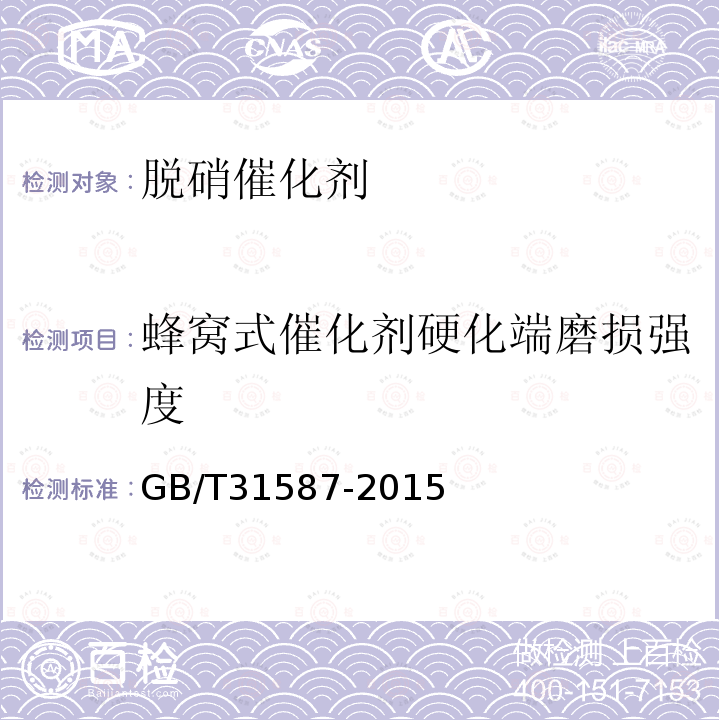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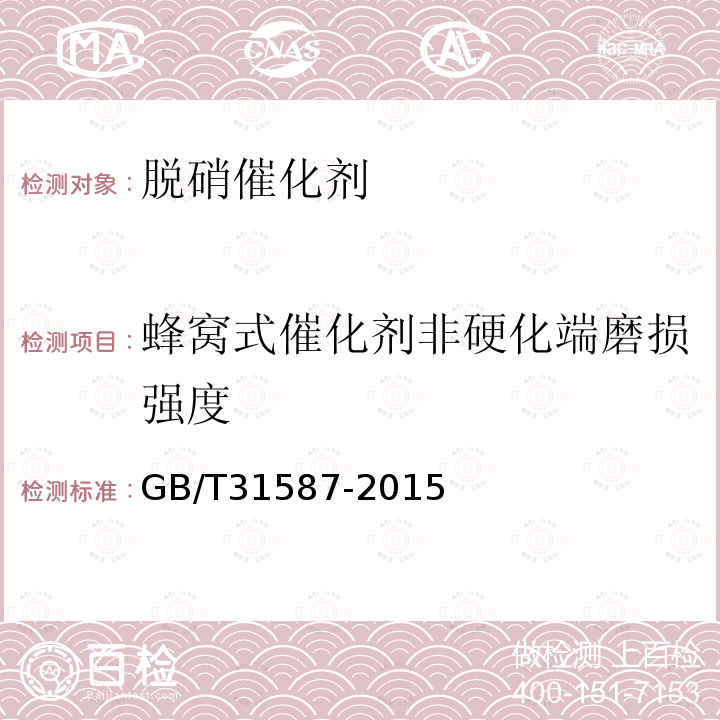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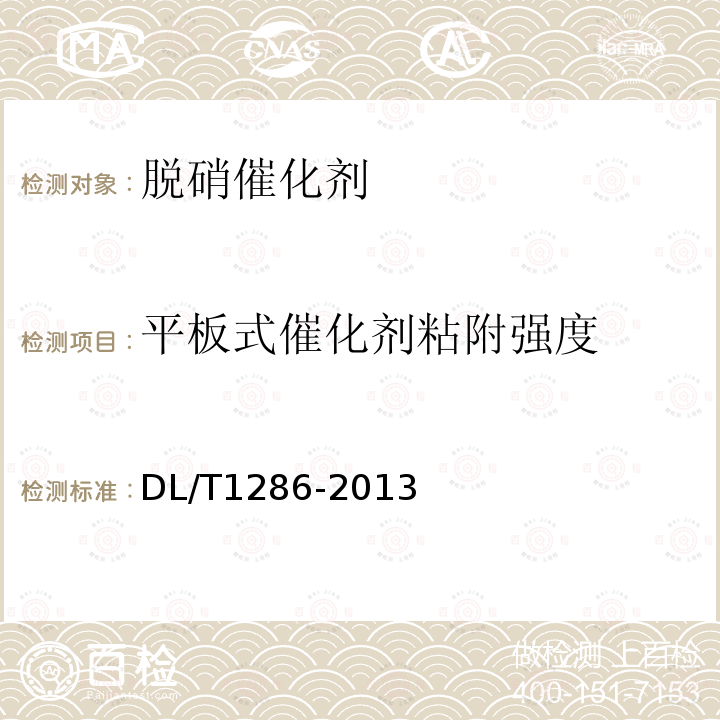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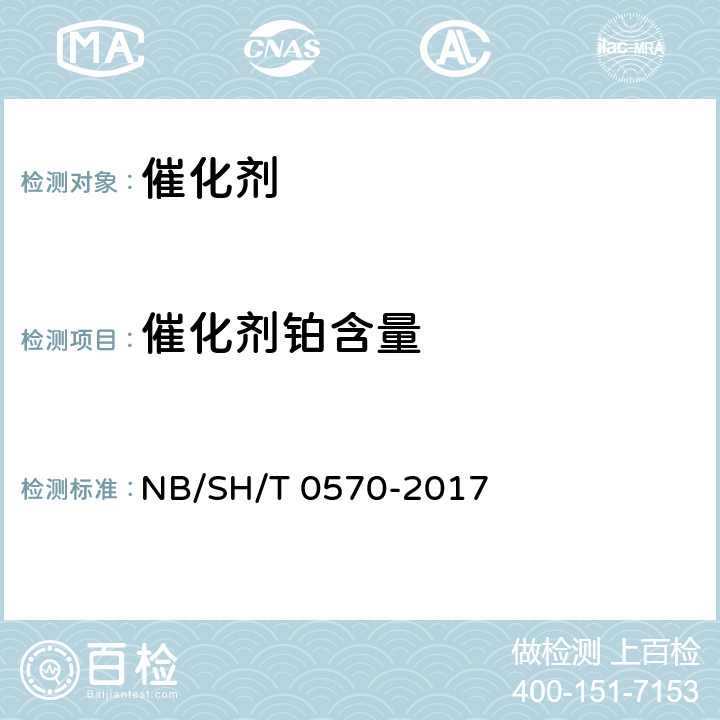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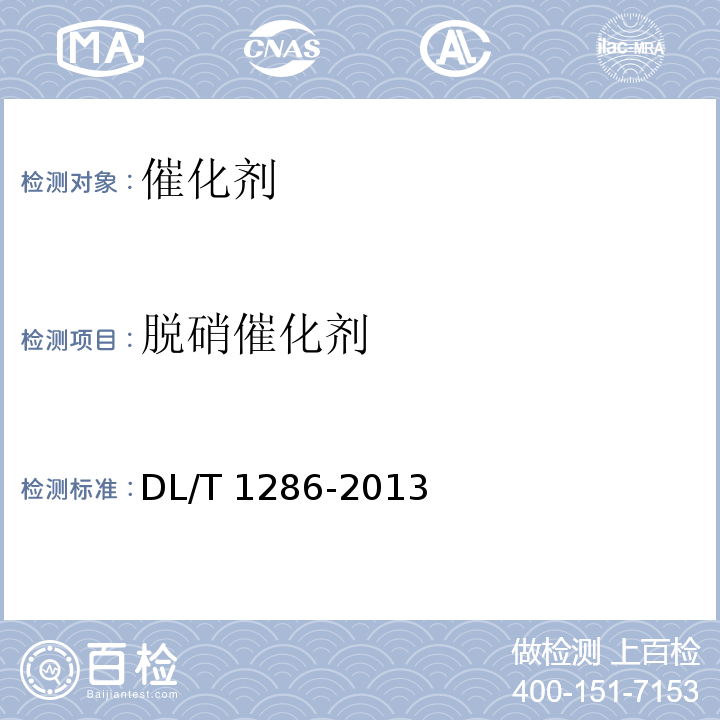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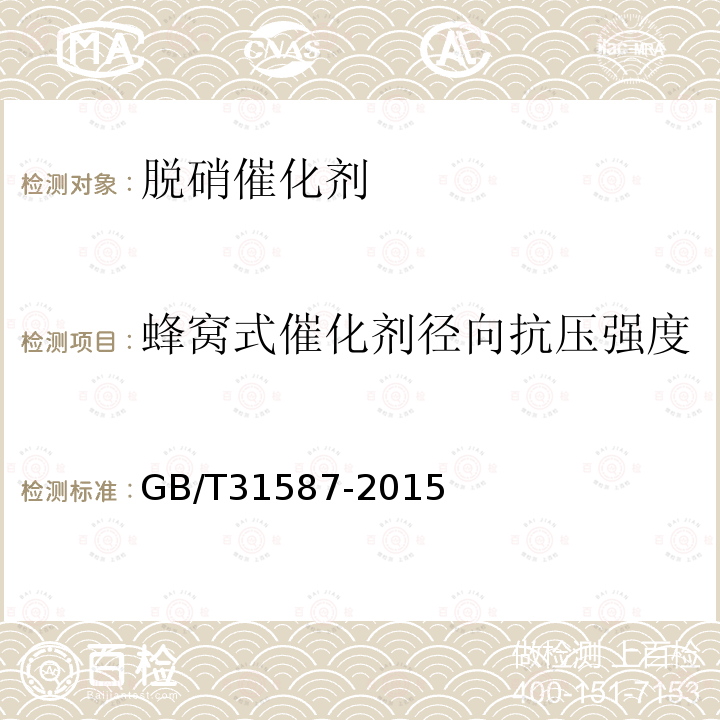








 400-101-7153
400-101-7153 15201733840
15201733840

